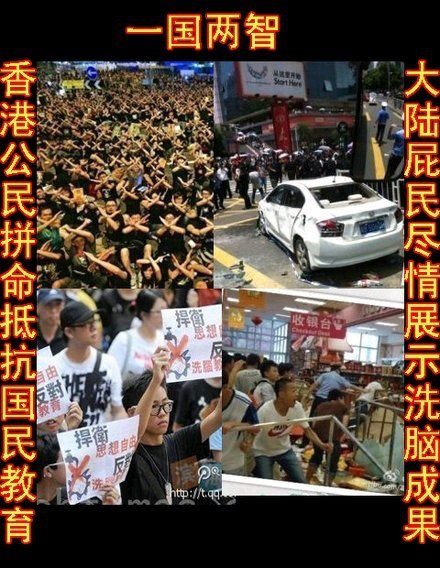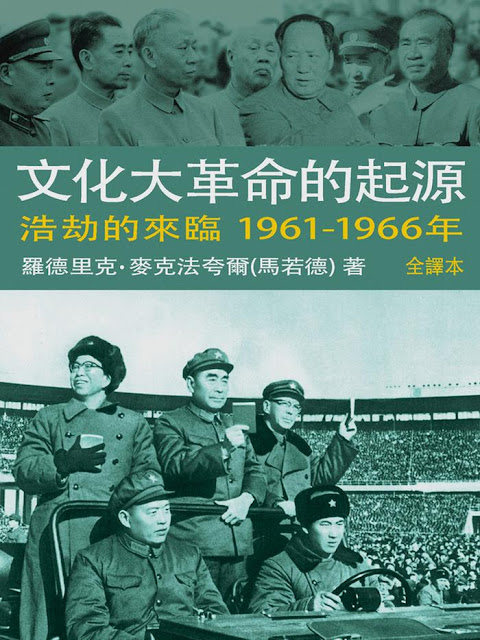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 张东园:鲜为人知的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
- 大卫・巴博萨问答:《纽约时报》调查报道幕后
- 格丘山:拔一草何助地荒?
- 張華:溫家財富被熱炒的影響
- 梁京:温家宝无法改变的事实
- 曹长青:温家宝家族巨富是真的吗?
- 陈破空:温家宝遭突袭,中共两派公开摊牌
- 吴澧:文化走出去,道德滑下来
- 润涛阎:为何温家宝没有27亿美元资产
- 林和立:中共高层有谁不贪?
- 张伦:绕着走的胡锦涛时代
- 罗小朋:中国的身份游戏
- 童之伟:风雨过后看重庆
- 余世存:梦惊天宇白 ――关于国运的一点想法
- 俞梅荪: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委员权力第一人
- 裴毅然:俞家三代一滴泪――祖迎、子死、孙冤
- 严家祺:从温家宝家族巨额财产看制定《国家政务官家族财产法》的必要
- 我的中国梦――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 胡少江:“入常”的寡头交易四规则
- 高瑜:“温家宝难以化解外媒引发的公关危机”
- 王力雄:解决中国西藏问题的钥匙
|
Posted: 31 Oct 2012 11:28 PM PDT
|
||||||||||||||||||
|
Posted: 30 Oct 2012 10:03 PM PDT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份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1944年2月2日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份留在大陆知识份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结语 任何人在任何一件事上相信了共产党的承诺和宣传,都可能在这件事上丢掉性命,这些留在大陆的杰出知识份子的悲惨命运就是明证。 ――原载:博客中国 |
||||||||||||||||||
|
Posted: 30 Oct 2012 02:02 PM PDT
《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上周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持有巨额秘密财富。以下是他对该报道引发的读者提问做出的回答。
问:
作为《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我想你在对中国的报道方面是一名老手了。我很好奇促使你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写?你有没有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卡萨布兰卡
答:
我2004年来中国,当时是一名负责经济板块的记者,主要报道经济能源、金融以及商业问题。在中国工作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高层政府官员家人在中国经济转型之际从企业得到所谓秘密股份的议论。上海、北京的银行业人士、律师以及会计师在一起吃饭时,这是个经常聊到的话题。很多人告诉我,这通常是利用朋友或者那些在持股人记录中很难看出与官员有关系的“代名投资人”实现的。有人告诉我,通常这些代名人替那些有权势的官员家人持股,使他们可以拥有一个公司的股份。
大约一年前,我开始写一个关于中国国有经济的系列报道,于是决定查一下是否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我开始研究几个高层领导人与商业的联系。任何了解中国商业和金融的人都知道,特别是关于总理家人的议论,一直都在流传,所以我最后的关注点就缩小在温家。我知道这非常耗时,而且任务艰巨,但还是决定要弄清楚。继续查下去以后,我大吃一惊,发现有大量与此有关的公开记录。我的报道并没有发现违法或者贪污腐败行为。但它的确暴露了隐藏在数十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投资平台背后的温家宝家人的名字。
问:
我几乎要相信了你报道中针对温家宝的所有指控(报道中大部分篇幅都指向他是一个两面派,并涉嫌严重的腐败),但在文章最后,你写到,他几乎要因为妻子引人质疑的商业交易活动而离婚,而且他还愿意让历史去评价自己。不幸的是,很少有人会把这样一篇长文读完,或者他们读完你的前半部分报道之后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请你告诉我还有其他读者,你如何解释自己的做法,即先给出强烈的指控,然后才暗示你并不确定这些指控是否属实。说的明白一点:我们都已经受够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腐败行为,但我恐怕你的报道会对读者造成误解,并引发政府进行更严格的控制——这意味着将来在中国会出现更多腐败以及偏左的政策。希望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美国西海岸
答:
您断言我是先列出了言辞强烈的指控,然后又暗示自己其实对这些指控并不确定,这一点我不敢苟同。
我写这个报道的目的就是要确认总理的亲属是不是在中国企业中拥有大额股份,弄清楚他们到底积聚了多少财富。如果有线索表明这些亲属是如何发家致富的,那显然就可以从中略微了解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亲属是如何行事的。
我没有进行指控,不过是陈述了自己的发现。根据我查阅的公开记录,过去十年来,总理的亲属控制了价值至少为27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
就和对任何给定主题进行报道一样,我们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调查。在我们追踪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些人名,我们直接去找了这些人。我们也多次试图联系总理和他的各位亲属,想让他们有机会同我们就这些文件展开讨论,或者反驳我们的发现。但他们要么不做回应,要么拒绝置评。那么,接下来最好的选择就是探究公开记录,和读者分享,总理在公开场合就腐败说过些什么,以及他是否谋求了个人私利。我们还援引了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文件,因为它们对我有所启发,因而可能会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发现的来龙去脉。其中,2007年的一份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电报很有意思,提到了总理以及他的家族的商业交易。
问:
首先,感谢能发表这篇文章。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我的问题是,对将于2012年11月8日举行的共产党权力交接,您的文章有着怎样的意义?显然,有人试图败坏温家宝以及他所属的改革派的名誉。谁将从您的文章中获利最多?是吴邦国和周永康领导的强硬派吗?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共产党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中,《纽约时报》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具。您的文章其实也不足为奇,中国领导层中谁的手都不干净,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整个政府都存在腐败。要当一名诚实的政府官员是不可能的。唯一令人惊讶的是腐败的程度。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几亿。多亏了《纽约时报》,现在我知道实际上是几十亿。 ——俄勒冈州本德市乔丹
答:
很抱歉。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商业记者,并不报道北京的政治动向,共产党代表大会也不是我调查的重点。所以我不能回答你关于这篇文章会带来什么政治影响的问题。或许你已经看到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裴敏欣(Minxin Pei)在文中的评论。他相信这篇报道将会在温家宝最后几个月的任期里削弱他的实力。另外还有两位这方面的专家——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Li Cheng)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可能会有关于十八大和这次领导人换届的消息。这次领导人换届将任命下一届的国家主席与总理,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将接手第一个职位,而李克强有可能代替温家宝成为新任总理。我在北京的同事正在做一个关于此次换届的系列报道,名字是“权力交接”( “Changing of the Guard”),非常引人入胜。
问:
很有意思的是,几天前,一些中国网站报道称,有人匿名将一大摞关于温家宝家人财富的材料交给了数家主要的美国新闻媒体。有人猜测,这是那些同情薄熙来的人士在报复。《纽约时报》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相关谣言已经流传了好几年之后,才决定在现在做这篇报道?此次的蓄意泄密事件是否跟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有关?如果是,我认为《纽约时报》应该对此有所提及。这篇报道颇具震撼性,但相关信息会帮助读者了解报道的背景。事实上,那样的话,我们将会了解到更多关于中国政治的复杂精细之处。——乔伊,波基普西
答:
你的问题很好。为什么现在?因为收集和评估这些证据需要很长时间,其中涉及了我们从各级中国政府申请获得的公司和监管方面长达几千页的公开披露材料。
去年年末,我开始调查温家宝家人的商业活动。之前,我一直在做一个叫做“审视中国模式”("Endangered Dragon")的关于中国国有经济的系列报道,我想写一篇能更深入反应中国资本主义在高层是如何运作的文章。这是个很宽泛的题目,所以为了更容易把握,我决定把焦点放在一个家族上。之所以选择总理的家族是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听到过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猜疑。人们公开谈论他家的财富,就好像这是事实一样,但却从没有真正的报道来支撑这些猜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没有人去求证这些广为流传的谣言。
因此,我去年就开始了,而且在大约一个月内,我就发现了有关部分业务非常有趣的地方。但每一项新的发现都要求进行越来越深入的挖掘。我本来预计,连带周末加班,我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计划,但实际上却花了一年多时间。
我看到了一些人的猜测言论,认为有“内部人士”给我提供信息,或者认为总理的一些敌人将一大箱文件扔到了我的办公室。这都是一些子虚乌有的说法。不仅泄密文件并不存在,我也从未在报道过程中见过任何主动提出或暗示说自己持有关于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文件的人。我只是在调查过程中对公开的文件进行了追查,如果我能大胆猜测一下的话,在我之前没有人走过这条路。
简而言之,考虑到这次调查所花费的努力,如果真有这么一箱文件,且包含了这篇文章需要的所有资料,我简直会目瞪口呆。若果真是这样,就太容易了。
问:
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细节丰富。我能问您一下,您是如何得到这么具体的信息的吗?您从内部人士那里获得过线索吗?在我看来,要在没有知情人士的任何暗示的情况下理清这样的秘密交易网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知情人士极有可能就是温家宝的敌人。谢谢。——纽约,杰克。
答:
我这篇长文唯一真实的来源是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文件柜。在历时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从中国不同的政府机构那里获得了这些文件。在最初成功地从多个地方的工商局获取一些公司注册文件后,我再接再厉,又查阅了数十家同温家宝亲属有联系的合伙公司的文件并支付了相关费用。
我也开始列出个人和公司的名单,试图弄清楚这些人是谁,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所有这些合伙企业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合伙企业中,很多企业的股东名单都很类似。
尽管工商局的记录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但中国记者很少真正地全面利用它们,而这些文件是有关私有企业的无价信息来源。《财新》(Caixin)和《21世纪经济报道》(21 Century Business Herald)这两家出色的中国出版物会经常利用工商局的记录,做一些颇具开创性的经济报道。然而,政府对有关高级领导人家人的报道进行约束,这导致中国的调查性新闻的深度与广度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涉及高级官员的家族时。
因此,杰克,没有“内部” 人士帮我。我阅读文件,打电话给律师、会计和金融专家,向他们咨询如何搞清楚这些记录的意义。偶尔,我会和能指认出某个股东的人见面。但我几乎没和人说过我正在写一篇有关总理的亲属的文章。即便是我的密友也不知道。我知道,讨论我的研究题目可能比较危险,这样做可能断送整个计划。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
||||||||||||||||||
|
Posted: 30 Oct 2012 01:24 PM PDT
纽约时报揭露温家宝的意义不应该理解为与温家宝过不去,而是从温家宝一草,知中国这块地全荒了。
温家宝只是区区一例,他还是比较爱惜羽毛的,属于中国官场的清流,所以绝对不是最坏的一例。排在后面的什么贾庆林,李鹏,胡锦涛等恐怕一个胜于一个。
如果纽约时报如果这时候再揭露第二例,中国政薹马上就会惊慌失措,魂不附体了,这就像当年给日本扔原子弹一样,扔第一颗,日本尚觉得偶然,还能挺,扔第二颗,它立即投降了,因为害怕还有三颗,四颗。 纽约时报如果这样做,纽约时报的笔杆子就可以兵临北京城下,直指中南海心脏了。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新的兵不血刃的世界奇迹,其有趣的程度不下于戈巴乔夫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集团。 共产主义貌似强悍,打蛇打到七寸了,它也很虚弱。 |
||||||||||||||||||
|
Posted: 30 Oct 2012 11:56 AM PDT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花了十個月去搜證,撰文揭露溫家寶家族至少擁有二十七億美元巨額財富。這是習近平之後,第二位政治局常委家人被外國傳媒供出其財產。今年六月,彭博通訊社指習家擁有三點七億美元資產。此時此刻,這些材料被公開,對溫家寶及北京政局將有深遠影響。
溫家寶妻子張蓓莉是「中國珠寶女皇」、其家族成員是平安保險主要股東、兒子溫雲松經營數十億美元風險投資公司、溫雲松與中國?星通訊公司關係密切等,早在網上傳開,而溫家商業王國的實際資產,也應遠較《紐約時報》公開的多,而比溫家財富更多、更不擇手段斂財的中共領導人家族,比比皆是,但文章對溫家寶的殺傷力,比誰都大。
對國內官員和知識分子來說,《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歷史悠久英美大報,公信力是非常高的。雖然很多中國人常抱怨西方傳媒以有色眼鏡看中國,甚至存心抹黑中國,但心底裏比誰都明白,外媒報道還是可信的,特別是有關中國的官員貪污、權鬥內幕、派系傾軋、民間抗爭等新聞,「出口轉內銷」才會有市場,即向境外傳媒放出有利自己消息,再傳回中國後就可影響國內的官意民情。這次報道後,「溫家富可敵國」再非傳聞,而是「事實」了。
溫家寶一直自詡生活儉樸(那雙波鞋穿了多年,跟礦工一起下井、吃飯,到學校飯堂與學生用餐等),也經常展示親民風格,成功建立了知民苦、解民困的「平民總理」形象,不僅讓他站上道德高地,成為推動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本錢」,更是他重要的「政治遺產」,他也希望史書如此書寫其十年總理任內的成就。
但這種形象跟他家族坐擁巨額財富形成強烈反差。溫妻、溫兒等家人或投資眼光獨到、運氣好等,才建立溫家的商業王國,但正如《紐約時報》報道,他們在溫總任內,財富累積的速度最快、收穫最豐,且跟不少國務院直接管理的大型國企有千絲萬縷關係。即使溫總沒施加影響力,但瓜田李下,溫永遠洗脫不了嫌疑,更何況地球人都知道:在中國經商,沒有過硬的後台,你的商業王國是不可能建起來,建起來了也很快就會被弄垮、瓜分!
因此,這個「事實」將溫家寶從道德高地拉下來,長遠而言會影響其歷史評價,短期則令他在中共內部無法強勢起來,在十八大人事等問題上的話語權也會降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中國傳統政治智慧,是有其道理的。
張華
——苹果日报
|
||||||||||||||||||
|
Posted: 30 Oct 2012 11:33 AM PDT
|
||||||||||||||||||
|
Posted: 30 Oct 2012 11:24 AM PDT
|
||||||||||||||||||
|
Posted: 30 Oct 2012 11:18 AM PDT
|
||||||||||||||||||
|
Posted: 30 Oct 2012 11:12 AM PDT
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读读外国文学的人能有多少?就是欧几里德平面几何,中国中学里如今也算教过一百多年了,搞不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大学生仍然大把大把的。文化的流入如此困难;即使西方社会当前的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我们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还是抱着长远观点。
莫言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少人预言: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愿如此。不过,文化的传输和渗透,在和平时期是非常缓慢的。前年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首都博物馆曾有纪念展,意大利方面还出借了拉斐尔和提香等绘画真迹。但利玛窦在中国,他想学习中国文化,还得答应一辈子不回国,不会将中国文字带回西方。在他留下的《中国札记》一书中,利玛窦批评了当时的中国人不会理性思维。为此他和明代大臣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但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三百年后之所以突然发生影响,那是铁与火的碰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即使签了条约,广州缙绅和市民,仍然坚决反对“英夷”住进城。因为英国夫妻在街上并肩行走,看在中国人眼里“伤风败俗”。随之而来的传教士,遭到中国乡土社会全面的、严密地抵抗。看他们的自述,他们几乎无法渗入清代社会。早上衣装整洁出去,晚上叫花子一般回来。走过村子,被庄户放狗出来咬,被小孩丢石头,被女人吐口水。读儒家圣贤书的大户人家,更是不接待。这种状况,要到八国联军打下北京、1901年签了辛丑条约之后才突然改变。敌视西方的那口气,突然泄掉了。人人都想知道,“洋鬼子”到底有些什么花样,打仗那么厉害?然后,传教士们才能将防疫针、体育运动、扫盲、作物育种、西方文学、现代医院和现代学校等介绍进来。
当然,后来又有长期闭关锁国,直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读读外国文学的人能有多少?曾在微博上见出版社的人说,北方一些省份的新华书店,对翻译作品的订购数常常是零本。就是欧几里德平面几何,中国中学里如今也算教过一百多年了,搞不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大学生仍然大把大把的。文化的流入如此困难;即使西方社会当前的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我们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还是抱着长远观点。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当然要依靠那些本民族文化修养很深的人。辩证法的另一面是,这些人也必须很了解西方文化。文化走出去,必然有碰撞。此其时也,最有说服力的,还是金庸笔下姑苏慕容家的战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曾在美国遇到一位很有古典文学修养、也很成功的华裔心理医师。笔者问:像你这样很古典的中国人,怎么开导那些美国人?他说不对不对,见到美国人,我就不是中国人了。他说,如果求医者是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求医者是天主教徒,他就是天主教徒;当然,如果求医者是中国人,他就是地地道道中国人。这位心理医师总是力图成为求医者的文化同类项,这样更有说服力。像他这样,疗程结束后,要是顺带讲解几句孔孟箴言,估计效果不错。
有些西方人来中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对国内道德滑坡的现状颇有看法,觉得这和想像中的中国文化相差太远。这时,你怎么办?披头散发,满地打滚,捶胸狂吼“感情被伤害?”比较能够让对方接受的方法,还是转到西方文化。今年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两百周年诞辰,你看他《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写的伦敦,外科医生让学徒在诊所附近路上撒桔子皮,行人滑倒后找他治摔伤;教区济贫所在晚上将垂死的老人运到其他教区,只为省去一笔丧葬费。工业革命导致城市急速膨胀,人们原有的乡土联系被切断,新的管理模式尚未完善,无道德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狄更斯后期作品里描写的伦敦空气之肮脏,煤烟之肆虐,今日读来也是触目惊心。此刻中国也在这一阶段,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可以说:我们也有作家很真切地反映了当今时代,建议读一读。
这不是拒绝外国人的批评。《雾都孤儿》写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1831-1901)初期;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已经以道德严谨为特色。狄更斯笔下,那些老派贵族——比如救了“雾都孤儿”奥利佛还敦促他学文化的几位淑女绅士——都是有文化、有道德的善心人。狄更斯并不直接引用教义,但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基督教道德仍然占有权威地位。英国当时有一个阶层、有一个标准,可以引导社会整体向上。而我们则面临着复兴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的艰巨任务。说到底,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更要在国内老树重花——不但根深,还要枝繁叶茂。
(本文平装版已于10月25日见报)
——《一五一十》
|
||||||||||||||||||
|
Posted: 29 Oct 2012 10:52 PM PDT
|
||||||||||||||||||
|
Posted: 29 Oct 2012 10:20 PM PDT
围绕「十八大」的权斗好戏连场。继薄熙来夫妇的丑闻与胡总心腹令计划儿子的「法拉利车震」事件后,中外媒体揭露了包括习近平与温家宝等大家族天文数字的家产。大陆稍微留意时事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共头面人物好像一身正气,天天喊甚么「八荣八耻」、要提高干部的党性教育、要当「二十一世纪雷锋」云云,但骨子里谁没有让配偶与儿女利用自己的高位去敛财?
《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家族的家财达到二十七亿美元后,美联社引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财务廉正」(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报告,透露去年中国暴发户通过洗钱等管道把高达六千亿美元运到国外。该研究计划更估计从二○○○年到二○一一年间非法流出中国的资金竟达到三万七千九百亿美元!其中当然包括薄熙来夫妇委託英国商人海伍德「处理」的不义之财。
其实中南海十分明白贪污腐败已严重蚕食中共本来已经体无完肤的合法性。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多次提到打击贪污与廉政建设牵涉到中共「生死存亡的问题」,江更明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对中共威胁最大的不是「境外反华势力」,而是党内的寄生虫。前总理朱镕基更有现代包公的美誉,朱总那句「做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送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更是中外闻名。但谁不知道老江的两位宝贝儿子做生意长袖善舞,身家过亿美元?朱总的儿女同样是商场的大赢家。当然,香港与外国的媒体没有刊登过这几位高干子弟触犯党纪国法的证据,但老百姓都晓得,假如他们的父亲不是国家领导人的话,这些阔少不可能富可敌国!
表面看来,胡温十年前执政后,搞过好几次廉政风暴,捉拿部长级或以上的大贪官看似比前朝多,但实际上问题没有改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经济的开放,无论财技与洗钱花招比过去高超得多。二○○九年底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上曾经有比较开明的中央委员倡议「干部阳光法」,即高级官员必须公示家族的财产以及直系亲属在海外的居留权与投资等。此建议当然没有通过!
今年三月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出事后便传出这位高干子弟居然拥有多部价值超过一百万人民币的豪华进口轿车,当时便有人提出要追查老令与他夫人的资金来源。但胡总却高调替他的家臣辩护,说甚么令计划「一天到晚忙於公务,没空管好家人」云云,结果中纪委并没有对令家采取行动。据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称,解放军的贪污情况更严重,他说「贪将」比「贪官」更厉害,对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习近平因为家族生意庞大,十八大上台后根本不可能采取果断的措施肃贪,看来中共这九十一岁老店就这样腐烂下去,直至灭亡为止!
林和立/ 中国问题评论员
——苹果日报
|
||||||||||||||||||
|
Posted: 29 Oct 2012 10:23 PM PDT
(张伦 法国塞尔奇•鹏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从满怀希冀,到渐渐失望,甚至因此无所作为,危机日积,威胁中国的未来而让有些人愤怒不已——最典型的莫过于张木生那句被人广为传播的“抱着定时炸弹搞击鼓传花”,人们对胡锦涛执政十年的感受发生很大变化,评价不一。
当初“涛哥挺住”的拥戴早已消失无形,“胡紧套”等嘲讽和讥骂充斥网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如果我们尝试着去对胡时代的施政风格做些归纳,在笔者看来,或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是一个“绕着走的时代”。
错失机会
事实上,对一个象中国这样处在巨变时代的大国的领导人,人们所冀望的,是他采取些具有决定性有助于民族稳步发展的、有前瞻性的举措,而不是弄些花拳绣脚,雕虫小技,修修补补。
遗憾的是,回首这十年,恰恰是因决定性改革措施的阙如,最让人诟病。且不说与邓时代,即使与江主政期相比,也是乏善可陈。至少江主政时期,还有加入世贸这关系国人迈向世界的关键性步骤的实现。而如有人提出十年来两岸关系上有些重大突破,那说到底其实是台湾方面的变化(连战登陆与马英九当选)所带来的。事实上,对一个象中国这样处在巨变时代的大国的领导人,人们所冀望的,是他采取些具有决定性有助于民族稳步发展的、有前瞻性的举措,而不是弄些花拳绣脚,雕虫小技,修修补补。
这十年,一方面,继承前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正面成果,中国在世人眼里显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另一方面,前期改革路线的偏颇所积下的问题正逐一显现,让这种“强大”又显得非常脆弱,需要领导人以其决断、责任心和远见推出新的政策加以修正,未雨绸缪,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引发重大波折,断送民族发展前景。
而就这点来看,胡执政十年错失了一些重大的机会和资源。
“绕着走”
客观讲,胡不是对问题茫然不知,否则,也不会有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五个协调”、“建设和谐社会”等政策的出台;一些具体措施的实施也不是毫无补救之效。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的调整,是要根治关系民族兴衰的痼疾,不是些治感冒伤风和外敷药能得以疗治。

现胡离任在即,希望未来的领导人不要再玩胡绕着走的游戏。
遗憾、指责或嘲讽或已都无济于事,为中国的明天计,需要的是探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教益以及观察未来中国可能演变的一些有益的视角。
一般来说, 分析一个政治领导人及其施政,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综合讨论:一是该领导个人素质与思想,二是制度因素,三是面临的历史情境与课题。 就前者来讲,我们必须直言说,胡不是一个有大魄力、远见的政治家。而这显然又是与制度因素相连的。对一个家庭出身并不好,受毛式教育,成长在诡谲险恶的毛时代,在邓那样的强人主政期始习政治的胡锦涛来讲,循规蹈矩,萧规曹随,借用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布迪欧的术语说,已经是他那代政治人物的一种“习成” ( habitus),一种第二天性。因此忍功可以非同常人,魄力却可能大为不足。至于毛时代的一些思想方式、语言也必然深植存续脑际。
众所周知,因体制使然,对中共大多数官员来讲,成功的诀窍在不出错,政治正确的前提是跟党走。不冒犯上级,不担风险,不负责任,有问题,能拖则拖,“遇见难题绕着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都是些是官员生存和发展的惯技。而在这种官场文化中浸染上升的胡锦涛,又怎能脱其痕迹?——国际上对其外交场合的拘谨木讷,拒人千里的印象,国内正式场面上的背书式演讲和套路语言,显然即是过去时代教育的后果,也是政治上缺乏自信和规避风险养成的习惯。
重要的是,强人离去、体制衰变,江系力量的掣肘等因素造成胡锦涛政治合法性资源和施政力量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胡锦涛步步小心,既要巩固权力,做点好事,又不要让潜在的对手抓住把柄,最自然的选择难免不就是这招“碰见难题绕着走”。
而2008年后国际和国内一些问题的急剧恶化,或许也更强化了他做这种选择的意识。何况,由于缺乏改革,近十年来权贵集团力量的进一步坐大,或许也会让他觉得无力回天。这一切,造成胡这十年“绕着走”的主要施政特色。
社会和谐论
胡执政十年错失了一些重大的机会和资源
这方面,最明显地体现在回避政改的“社会和谐论”上。显而易见,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缺乏公正,社会矛盾激化。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显然是在政治领域。但恰恰在胡主导下,不去正面触及政治这根本,却绕个圈来大谈社会和谐,显然,即使不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药不对症。
更糟糕的是,由于绕着走,不去进行新的政治制度建设,而政治领域的问题毕竟又无法全然用其他手段解决,结果在政治领域强化现有政治机器,甚至启用恢复一些已经放弃淡化的旧招数来应付局面便逻辑地成为选择。
这就是我们看到胡时代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一些强调党的权力,用专政机器来控制社会人士等做法死灰复燃,得以强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谐”迅速地沦为“河蟹”,成为讥讽、嘲笑甚至是社会反抗的对象也就毫不令人奇怪。
至于经济上不去下大力根治内需不足,结构失调的痼疾,满足现得利,借着入世得以强化的经济发展上外贸依赖过重的问题变得积重难返,在外部经济环境危机下只得再打国家投资的刺激强心剂,长期吃惯了国家投资、房地产等补药的虚胖经济病上加病,这些也是有目共睹。
“保江山”
多年前,有朋友谈及,一位与胡锦涛有相当接触的人士曾在与他论及胡的执政理念时,将其概括为“做好人,保江山”。“保江山”自不用解释, “做好人”,即在可能的范围尽量做些好事。这些年来胡执政的轨迹,可见这个概括不是无中生有。倒可能确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胡的内心想法。
问题是,这位朋友当即向该人士指出:如果“保江山”与“做好人”矛盾时该如何处置?对方无言以对。事情的关键恰恰在此,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或许“保江山”与“做好人”可以暂得妥协。但当“江山”(现体制)是许多问题、坏事的根源时,保江山就只能是做坏人。胡离任在即,但这个“做好人”与“保江山”之间的矛盾不仅依旧,且越来越尖锐。但愿,念天下苍生的福祉,为民族也为个人的利益计,未来的领导人不要再玩这种绕着走的游戏,而我也相信,事实上,他也再没有胡玩“绕着走”的运气,是到了必须直面问题的时候了。
十年后,我们将会怎样再来概括新领导人的执政呢?
|
||||||||||||||||||
|
Posted: 29 Oct 2012 10:29 PM PDT
本文为"乡村中国讲坛"第一讲文字实录,已经罗小朋老师本人审订,共识网独家授权发布
主讲人:罗小朋(著名经济学家)
主持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讲坛时间:2012年6月9日上午 讲坛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讲坛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乡村中国读书会"
近年来,身份(identity)这个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学科和学者的重视。这个现象绝非偶然,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人类合作秩序之重要,而理解和促进人类的合作,正是21世纪人类的主题。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样的身份游戏中。虽然有些身份,如性别和种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现代生活给地域、宗教、职业乃至政治和社会身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性和流动性,各种身份之间的互动和转换空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身份游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性别和种族身份游戏在内,都处于快速的演变之中。不把身份概念和规则引入社会研究和分析,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诺贝尔经济学得主G.Akerlof在他合著的新书《身份经济学》的导论中就指出,今日的经济学已经不能仅仅把自己限于消费和收入的研究,而必须考虑多种社会动机。身份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就是人们的身份意识决定了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预期,而这种预期对于经济如何运转十分重要。
身份游戏遵循的规范不仅体现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也体现了历史事变和文化习俗的约束。因此,每个国家的身份游戏,都有极其鲜明的体制、文化和时代特色。过去的百年,中国人争独立和自由的激荡历史彻底重塑了自己的身份游戏。与传统的身份游戏相比,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在集体性和公共性方面,有了巨大飞跃,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地位也因此而大为增强。但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还不是自由人的游戏。中国人何以增强了集体性和公共性,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这种不自由的集体和公共生活如何可能?这样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形式是否可以持续?中国人又如何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把外源的、强制的集体性和公共性转化成为内生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真正的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我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在不断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身份游戏”的概念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变化非常快,挑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回首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常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三十年前,我是79级的人大工业经济系研究生,那时候,我们住在东门一进来的主办公楼里,那一年我们系就招8个研究生,住在一个办公室里,没有宿舍。现在高楼林立,我刚才和仝老师讲,其实我们当年是第一批学生到新华门去游行,那个政治氛围有点像二十多年前的那个事件一样。那时我们闹的是把二炮从人大校园里赶出去,结果也闹成功了。当时,我记得那些外国记者围着我们,同学里面有人能用英语跟外国记者交谈,我很羡慕他们,什么时候我的英语能那样。几十年的变化,真想不到。 言归正传,首先什么是身份游戏(identity game)?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玩多种身份游戏,我们有文化身份,国家和民族身份,有地域身份,有职业身份。你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就要玩这个游戏,就要知道在你的身份里面包含着:一个是“权力的游戏”,在你的身份群体里,权力博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谁看过维特根斯坦的东西?应该看一点,不一定要去看他的原著,有一本中英文的小书介绍他,可以去读。他是整个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开拓者。他有一句话非常深刻,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在你置身其中的身份游戏中,很关键的一个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一个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你懂了这个,你就懂了你这个身份的语言游戏,也是身份游戏最基本的部分。 让我就先介绍一下身份游戏的概念。身份游戏的起源,为什么扯那么远呢?因为这也和当前国际上社会科学的趋势有关系。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共同创造新秩序的问题,所以那个老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身份是从哪里来的?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中国很多人还没有这些当代的常识。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常识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常识是什么?那就是人类对自己怎么来的已经有了一个和二十世纪很不一样的认知,很不一样的知识基础。不管你是哪个文明,哪个文化,这些新知识应该是大家共有的知识基础。 这些知识有一些很晚近的发现和新假设,包括西方学者的争论,比如说文化演进最基本的机制是什么?几年前,包括最近福山的那本书,一些学者认为血亲选择(kin selection)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上次回国做报告还用了这个观念,但今年4月份出版的Wilson的新书,他认为血亲选择作为人类文化演化最基本的机制已经被否定了。西方学者做了多方面的验证,包括有人从数学上来论证血亲选择机制不成立。当然还没有一个所谓终结性的结论。 所以,我今天也推荐Wilson的这本新书,我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需要的关于人性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书名是The social conquest of the earth。Wilson把这些年来关于人类演化的这些新知识综合在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他个人的观点,其中包括对宗教的批评,是很多美国人不能接受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身份意识最早的起源是部落文明。部落文明塑造了人类共同的人性与合作的文化本能(移情能力和语言能力等),这个结论现在是有实证支持作为基础的,包括基因考古的研究成果。 根据这些研究,人类进化的身份游戏也好,文化秩序也好,制度也好,根据Wilson的观点,推动演化的有两个最基本的机制,一叫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一个叫个体选择(individual selection)。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关于文化制度的讨论归结为这两种选择机制的组合和构造问题。 人性的矛盾就表现在它又是自私的,又是利群的,现代研究表明这两方面都有其基因根据。Wilson认为,人类的铁律就是自私的个体打败利他的个体,比如像雷锋这类人。个体之间的竞争,自私者必胜。当然不是最自私者必胜,因为个体竞争受到群体竞争的约束。群体之间的竞争,是团结的、利他的群体必胜。否则的话,就不能解释今天人类存在下来的社会为什么是现在既有自私的人也有利他的人这种形态。如果一个群体里面自私的人永远占上风,这个群体还能打赢其他群体的话,今天人类社会就全剩下自私的人了,但事实是人类社会今天还有不自私的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总体看,群体选择机制主导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身份意识是人类群体生存方式的演化产物。 二、“身份游戏”的历史渊源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既然人性之初基本上差不多,那后来的文化和制度为什么差异这么多,这么大呢?回到中国文明,我们跟其他文明一样,起点都是部落文明,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国家起源于部落文明的整合,打仗、兼并,这个也没有错。在整合过程中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打败了一个部落,打败了一个小的文明,打败了一个群体,怎么办?这个问题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里面明确提出来了。说穿了就是被打败的部落,有它的身份意识,有它的文化。马基雅维里说,无非是三种办法。“第一种是摧毁它们,第二种是征服者亲自去住在那里,第三种是让他们继续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使用的是第三种办法,而罗马对希腊人使用的是第一种办法。马基雅维里对第二种办法语焉不详,因为欧洲古代文明没有第二种办法的典型例子。实际上中国文明恰恰走了一种中间路线,这就是我们的西周。 任何一个新的身份游戏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尤其是战争、革命,可以重新塑造人的社会身份。所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导致身份游戏的一种嬗变。西周伐商是整个中国文明身份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有记载的起点。一个概念起了重大的作用,就是“天命”观的确立。许倬云教授认为这与周人一场辩论有关。因为周灭商,得到了一个统治整个中原的机会。为了为这种统治辩护,你要有一个说法。天命的说法很好,就是天给了周统治商原来势力范围的正当性。但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周人辩论的最后结论是天命降于周王,而不是降于周人。这个政治结果就使得我们中国文明和犹太文明不一样。犹太人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就是说天命降于犹太人,并不是降于犹太王。按照许倬云的意思,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这场历史性的辩论后果之中,因为我们中国人统一的文化身份就是从这个天命来的。天命是降于王,而不是降于一个族,一群人。这样就使汉字文明的文化身份有了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你只要认这个统一的王,我们的文化身份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就此埋下了中国人身份游戏的根子。 当然,说法是这样,背后还有内在机制。我的理解,汉字的传播对中国大一统的身份游戏影响很深刻。主要就是汉字传播对瓦解部族的集体记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部族文明有一套口传文化,口传的信仰系统。来自不同部落文明的人,一旦学会汉字就进入到个人机会更广阔的一个大文明共同体内,容易把自己部族文明里的东西忘掉,或者撇下。杜赞奇对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很深刻。他讲中国人的信仰结构,精英和底层是两截子的,是一种上下相隔的纵向构造,跟其他很多文明不一样。我认为,这和汉字在中国的身份游戏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不过,西周还留了一条部落文明的尾巴,就是血缘神性。(帝王将相是有种的)春秋战国,血缘神性很重要,在古代的宗教和贵族精神的形成中很重要,但血缘神性在我们中国文明中消灭得比较干净。在部落文明里血缘神性是显然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部落有神的力量在支持。但在中国文明里,血缘神性从春秋战国开始,由于汉字传播提高了人的社会流动性,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期间一个重要的身份游戏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认字的阶层,这对我们整个文明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文明是开放的,你只要认字就进到有地位的阶层来了。而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思想那么样精彩,现在说那时候天下大乱,死人很多,但思想的传播在汉字的文明圈里不受太多限制和操纵,思想只要在竹简上抄下来,就可以传播开来。孔子说那些话有人抄,所以传播开来。只要你的思想有吸引力,就有人抄,就传下来了。 这不像后来,后来有人可以控制。到了吕不韦他就想控制这个东西了,让人写书。但之前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思想是属于完全自由的竞争状态,这就是百家争鸣的背景。一旦进入了控制,就不一样了。这个控制实际上从秦就开始了。在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怎么解决被征服的部族文明,或者领土的治理问题,中国人给出了一个马基亚维里想不到的解答。那就是用游士,用别的地方出身的知识人来治理被征服的土地,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不用本土的,也不见得用直接从我这个国家派来的,而是用天下游士里面选择的知识人,这是郡县制最实质的内容,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治理机制,这也是秦一统天下的一个制度基础。 这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罗马帝国征服许多国家以后,它始终也想解决怎么统治,怎么控制的问题。它搞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搞了一个citizenship。对被征服的土地,允许一些人通过效忠帝国获得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就是今天我们也在讲的公民权,身份权。这个不是很成功。所以,最后才走到基督教这条路上,利用统一的宗教信仰。因为基督教当时已经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它为什么原来杀基督徒,后来又转过来了,就是发现公民身份不成功,这是刘小枫讲过的,用公民权来一统天下的办法走不通,才走到了利用基督教统一信仰。你们去对比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和中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很有意思,这里面有不同的身份游戏。 所以,到了秦汉,中国的身份游戏就定型了。我应用Wilson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个体竞争是不封顶的,就是血缘神性失去了以后,人皆可成舜、尧,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我们的文明范围里面,天下失鹿的话,人人皆可逐之了,是这么一种身份游戏。这个概念不是在所有其他文明里都有的。 另外,我们是家国一体,到秦汉以后,中国文明的家和国是同构的,它的包容性很大,只要你认同儒家的等级伦理。但是,这个东西造成了一种反政治倾向(赵汀阳)。一旦没有了(身份平等或政治人格平等)群体,也就没有政治了。中国的大一统,就是把内部(群体)政治自主性,系统消解掉了。所以,中国的身份游戏彻底解构了部落文明的群体文化特性,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用精英选拔的开放性来强化个体和家庭之间的竞争,压制非血缘性群体的凝 聚力,瓦解群体的政治自主性。 这样的身份游戏是有很多问题的。我开始讲到,部落文明它形成了人类文化心理本能,那种激情,互相的道德和情感的支持。而大一统的身份游戏难以满足人类在部落文明时代形成的许多文化心理需求,导致了集体的宗教生活之退化,情感和道德相互支持的退化,荣誉(英雄)机制的退化。所以,我们跟西方文明的区别,或者跟其他许多文明的区别,可以说是他们更多地保留了部落文明的一些东西,而我们把部落文明的东西消灭得比较厉害。像荣誉机制,中国不是说没有,但是比较弱。儒教是把家庭内部的伦理变成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家庭要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本质的要求,不是平等,家庭里面不能搞平等,否则跟个人基因要往下传的本能冲突。所以,福山在他的书里就讲,基督教对家庭有解构作用。 一种身份游戏必须要能够不断把自己再生产出来。探讨一个秩序它有没有生命力,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精英选拔的开放性,在维护垂直整合的精英选拔的开放性上,中国文明是一直在进化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机制。我觉得孔子开辟的私塾教育,是这种秩序能够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前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是多元的,到西汉以后这个思想就完全是统一的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支持大一统的儒教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大一统和儒教的主宰地位与土地产权的安排也是结合起来的,在中国,这个秩序游戏,身份游戏的再生产,是跟一种分散的土地产权有内在联系的。总的趋势就是下层的人向上流动性是不断扩大的,贵族的活力是不断下降的。 但是,这种秩序再生产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皇帝的选择就是一个问题。王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还把这个问题搞砸了。这样的话,改朝换代就变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再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改朝换代机制出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们知道东汉以后,中国打来打去,就是统一不了。(分治稳定不下来),统一了也不稳定。原因没有人深究。日本有一个学者就专门研究封建领主制为什么不能够在中国确立,因为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发展得很成熟。这可以看到我们汉字文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的文人不信分裂,不信分治。即使是处于分裂状态,信仰的还是大一统。 但文人也有一个弱点,他们没有本事重建统一。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中国文人精神上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状态,(这恐怕)跟我们民族知识分子这个弱点有关系:你又信大一统又统不起来。(看看诸葛亮的命运)所以,后来大一统的重建,周边的部落文明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中国文明要借部落文明的血性和活力来重建大一统,包括北周改造自己的文化(来重建大一统)。再就是隋唐重建大一统,都有这些部族文明的作用。但是,中国文明有自己的长处,它的治国理念是轻傜薄赋,高度分散的土地产权支持了普遍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支持了经济竞争。自治的农村社会支持了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以农村自治,以水网作为运输系统的这样一个市场系统,它的构造非常奇特。施坚雅就是研究中国独特的市场网络,在世界博得了很大名声。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市场构造理论。 而且中国的社会网络也很重要。我们的地缘身份在政治上不是很重要,但地缘身份一旦进入到市场游戏里面,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清时代同乡在商人组织方面起很大作用。晋商、徽商,地缘身份虽然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隐性的,但在中国的商业中,这种社会网络起着维系市场信用的作用。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开放性,不那么封闭。但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弱点是公共性不足,没有地域政治共同体的支撑,它的公共性是不足的。 所以,李约瑟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已经被新的知识(包括语言与秩序建构的关系)解决了。因为中国文明这种构造,(包括它的语言游戏)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当然不能因此而低估中国知识系统的价值,这是两码事。我们不可能产生西方这套科学的知识系统,但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有很重要的认知价值的。这个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包括中医这一套,它的价值是会越来越高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身份和语言游戏玩不出科学来。 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逻辑(表达)能力不足,这是致命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身份游戏(和语言游戏)逻辑能力不强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的一个简单解读,就是中国差序的文化秩序。发展逻辑表达(要求对话者彼此承认人格平等)对维持等级秩序是不利的。说的直白一点,你要讲逻辑,很容易让身份高的人没有面子。 |
||||||||||||||||||
|
Posted: 29 Oct 2012 10:27 PM PDT
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必须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十八大有必要从根本上否定“重庆模式”。红色民粹主义是“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构件,否定“重庆模式”首先要在理论上揭示红色民粹主义的反民主、反法治、谋特权的内容和极端性质
2012年9月21日至9月24日,我应朋友之邀,到重庆进行了为期4天的讲学和考察,那时薄熙来先生还没有被“双开”。回来后,我把自己那几天的一些见闻和感受整理成文,这些文字或许可供对重庆事件感兴趣的读者参考,也可算是我对曾关注拙作《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的读者所做的一点回应。
一、城市建设成就和资金来源问题
这次去重庆首先关注的是城市建设。与5年前相比,重庆的马路、街道变宽了,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大都新而气派,不小程度上拉近了与沿海大城市的差距。从住宅小区的外观和我具体接触的一些重庆居民的居住情况看,市民的住房条件较过去有显著改善。毫无疑问,过去几年重庆的城市建设成就不小。
但这个城市过去几年建设投资数量惊人。在重庆的那几天,我经常提出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的。较多人说资金主要是薄先生凭其个人关系从某银行借来,少部分来自税收、卖地、转移支付和“打黑”。不过,大家在以下方面似乎有共识:重庆过去几年一直在大举贷款,完全不管此后拿什么偿还,以及是否有能力偿还等问题。重庆地方财政过去到底透支了多少,贷款多少,在民间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当地人普遍认为,薄能把钱找来就是本事,不管是转移支付还是贷款,工程搞完了再说。还不起吗?还不起或许就不用还了。为了重庆的稳定,说不定到时候会用国家财政填重庆的窟窿,由全国人民为重庆城建埋单。“外国的债务都可以免,何况自己国家的一个直辖市呢?我们不怕欠债!”这类思维很普遍。
有朋友对我说:“百姓不懂收支关系,财政问题,他们只看眼前,眼前有好处他们就叫好,不会考虑什么透支,什么钱怎么还或由谁还的问题。”这或许就是神话背后的市民心理依托。要揭示薄的城建政绩神话并不难,正如最近童大焕先生所言,只要搞清楚和公布这几年重庆的“钱从哪里来?是转移支付?还是致命的透支?抑或是以打黑名义进行的黑打敛财?只要钱的来路查清,城建‘奇迹’的来龙去脉就全部清楚了。”
二、市民安全感消长与情绪两极化之根由
在重庆,很多人和我谈到安全问题,一部分人强调薄主政时期安全改善了,另一部分人说薄、王时代很恐怖、很不安全。我看,他们说得都对。
薄、王时期,公权力强化治安,有效减少了地痞、流氓打架斗殴、欺行霸市、偷鸡摸狗等治安问题,连站街女郎都几乎绝迹。社会治安好于过去,这一点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也曾是重庆官方持续宣传的亮点。
但是,城市治安好转的代价很大,除难以持续的超额警务支出外,最大的代价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在社会治安好转的同时,警察权等公权力对个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财产权的侵害与日俱增。重庆政法系统多人告诉我,薄、王时期,每年都自上而下给各区下达必须完成的计划指标:规定每个区必须送多少市民劳教(一般上百或数百),必须刑拘多少人,必须给多少人定罪判刑,必须找出和打掉几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任务自上而下压得很紧,实际上是变相逼迫各公安分局、派出所人为制造种种冤假错案,包括打黑假案。至于薄、王时期公民私人财产权受到的威胁,普通市民可能难以感受,但民营企业家对此也许刻骨铭心。
我曾多次请教重庆政法系统官员和一些法学院师生:在薄、王时期,普通百姓难道感受不到来自公权力的巨大安全威胁?记得有一位法务人员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百姓们只看到地痞流氓少了,没感到自己随时可能因一点小事会被抓去坐牢、劳教,甚至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等他自己感觉到这种危险降临时,已经晚了!”
我相信,在薄、王时期,公权力违法乱纪滥施暴力给市民带来的安全威胁在总量上可能大于他们为市民消除的来自地痞流氓黑恶分子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就安全而言,市民在总体上失大于得。但就个人而言,其感受和际遇会截然不同。
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重庆民众对打黑呈现明显的两极化情绪,但酿成两种截然对立情绪的原因,都在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一方面,由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公权力机构对一些横行霸道、侵害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人员该处罚的不处罚、该抓捕侦办的不抓捕侦办,导致受害民众及其亲友产生极端的情绪,即只要说是打黑除恶,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刑讯逼供还是被错抓错判错杀,只要尚未轮到自己头上,都一概拍手叫好。另一方面,同样由于警方或司法机关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办案搞刑讯逼供,违反程序正义,致使一些无辜的公民被劳教、被错抓错判等种种情况。这些情况造成蒙冤受屈者及其亲友产生另一种极端情绪,即不分青红皂白质疑乃至否定公安和司法机关“打黑”办案的正当性、合法性。
所以,建设和谐、公正的社会,必须有效降低民众的上述两种极端情绪。关键在于公检法部门在办案时都要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严格依法办事,包括落实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保证被告获得律师充分辩护和法院真正实行公开审理。
三、“唱红”及舆论购买
我一直认为,“唱红”是以冠冕堂皇的外在形式,悄无声息地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往“文革”方向引领,悄无声息地否定着宪法原则、否定着中共党章确定的路线、方针。而其动用人力财力的途径,则直接破坏了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和国家法制。据我在当地了解,重庆在“唱红”方面的投入是相当巨大的,在市区两级财政中,其比例高得离谱。另外,在海外和国内,用于“购买”宣传服务的资金支出,仅从已经透露的数额看,就已经相当惊人。
我在重庆了解到,当时为鼓励各地学者为“重庆模式”张目,有些机构相当慷慨大方。我获知的标准是,当地学者参加座谈会,签个名,发5000元,外地牌子大的学者,参加一个座谈会说几句,主办方出手就上万元或数万元。当然,差旅费也是重庆出。不论怎么说,如此“购买”特殊“劳务”,实在离谱。
我觉得,中国公众和重庆人民有权知道,这些钱到底是用于办公益还是谋私利?这些钱哪里来的?哪些人拿去了?一个市委书记凭什么不经各级人大批准可以在预算外动用成百亿上千亿的资金为自己造势?有些地方的干部为在当地差额选举中能当选,变相给部分人大代表送点小礼,或发手机短信拜票,就被认为违反党纪政纪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但薄为了上位,动用成百亿上千亿元的公款搞政治腐败,怎么就没有阻碍呢?
四、在“共富”口号下对私营企业的劫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走向共同富裕,还不可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薄熙来在重庆鼓动的,恰恰是在现阶段就兑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初级阶段的极左口号。这个口号还有一个妙用,那就是用来证明劫掠私企老板财产的正当性。
记得我撰写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受到了重庆市委党校一教授的强烈批评,被批评的核心内容,是我的报告把彭治民、李俊和陈明亮三位认定为重庆净资产最多的民营企业家。
我的研究报告认定彭治民先生是重庆最富有私营企业家,是站得住脚的,至少不是“妄说”。重庆公安局091-618专案组组长王智在重庆卫视2010年11月播出的《拍案说法》节目中说得很清楚:彭治民是重庆最大的地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财产是46.7亿元,由于土地已经增值,彭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在100亿以上。彭的律师余晖告诉我:彭的财产被查封冻结时光现金就有6亿左右;彭治民案被冻结查封资产总值在100亿、净值在70亿左右;彭旗下还有一部分财产未被查封,现在其妻子和亲友掌握下。我综合判断,彭整个公司资产净资产按当年市值计算应该在84亿上下。这个数字高于胡润排行榜上重庆首富尹明善先生的68亿元。
从重庆“打黑”对私有企业的剥夺情况看,非上市房地产私企有钱、有地,打他们特实惠,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倒下后社会影响面小,所以他们往往成为被打的首选。
重庆“打黑”变成重点针对私企的“黑打”,恶劣影响远远超出了重庆范围。诸恶劣影响中之最严重者,是加剧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和私营企业家向海外的移民。
五、党的领导蜕变成了个人独裁
在重庆四年,薄氏在重庆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大搞个人恐怖独裁,中国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完全不足以制约其违法乱纪行为。重庆当地人也好,北京人、上海人也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其妻子故意杀人的事实因偶然因素败露,薄氏的“司马昭之心”几乎肯定会变为现实,其结果必然是给国家稳定和执政党带来无穷祸患。
上述情况的出现,不小程度上是因为当事人的个人品德缺陷。领袖人物的个人品德和才干对社会和国家的治乱有着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有学者将薄氏比拟为春秋时期晋国的卿大夫智瑶(亦名荀瑶),意指其长处不少但少德不仁,此说应该算比较中肯的评价。
但是,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看,薄氏和重庆事件,最主要地还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病造成的。一部宪法和几百部法律,其权威居然还抵不上薄氏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在现行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地方党委,地方党委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委书记。在这种体制下,党委书记及其领导下的公权力体系,是不是遵守宪法、法律,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宪法、法律,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政治素质或为政道德。一个行政区域,如果任职的党委书记政治素质或为政道德较高,一般会实行开明专制,会比较尊重宪法、法律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反之,这个行政区域就会出现党委书记的个人专制,其能力愈强,个人专制程度就愈深、花样也愈多。
我们看到,薄氏在重庆任职的那几年,实际上实行的是薄氏个人的极权专制。
六、法制蒙受了浩劫
从已经披露的部分情况看,“打黑”不过是薄氏为条件成熟时在全中国实行个人恐怖独裁做的一次预演。
薄氏目无国法党纪、恣意妄为、指鹿为马、当面撒谎、睁着眼晴说瞎话的“能力”,在我亲历的中国过去50多年中前所未见,其践踏自由、生命和财产等公民基本人权的肆无忌惮程度,让几乎所有人心惊。我这次在重庆考察,从不同来源了解到人们对薄氏在重庆搞个人独裁的一些反映。
那里任何人只要敢批评他、顶撞他,轻则劳教,重则受刑事追究,罪名随意安放,证据怎么方便怎么找,因为公安的整个领导层差不多都是他的家奴。黎强数以十亿计财产被充公,判重刑,主要就是说了一句顶撞薄氏的话。
那里按人口比例自上而下下达劳教指标、刑拘指标、定罪判刑指标。一个区一年要侦办3个还是5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要劳教200人还是250人,要刑拘判刑几百人,都有事先下达的刚行指标。
那里号称“零上访”,但冤假错案成堆的地方何以能“零上访”?真正的秘密在于,当地公权力不惜把判刑、劳教作为遏制上访的最方便手段。所以,中国上访最多的地方不一定是基本权利保障最差的地方,上访最少乃至零的地方,倒可能是基本权利受践踏最严重的地区。
那里的酷刑在21世纪的当代恐怕要当之无愧地数第一。过去只知道铁山坪、吊打、嵌进肉里的手铐,熬鹰、冷冻、电击、饥渴,虫咬,这次了解到还有铁制“太平椅”——无论寒暑,被抓来的人坐在上面,四肢固定在特定位置,吃喝拉撒睡都在上面,最长可达数月。
那里的私人财产权在薄氏公安系统的家丁式警界高官面前毫无保障。随便找个理由,私营企业家数亿数十亿的资产和家财可能就会被查封罚没,不需要审判,也没有收条清单。数以千亿计的私人资产和财产,大多没有依法处置,现如今大都去向不明。在这种情况下,薄氏在公安系统的家奴们监守自盗、职务侵占、徇私枉法,无所不为。
我接触到的重庆内外的法律、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薄熙来的个人恐怖独裁让重庆的法制状况倒退了几十年。
薄氏做市委书记时期重庆的宪法、法律实施状况,向人们展示了现行政治法律制度因为党委书记权力无制约而整体失灵的情况。
七、总感觉:深化改革必须从根本上否定“重庆模式”
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必须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十八大有必要从根本上否定“重庆模式”。红色民粹主义是“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构件,否定“重庆模式”首先要在理论上揭示红色民粹主义的反民主、反法治、谋特权的内容和极端性质。
红色民粹主义的极端性在于,它忽视、否定少数人利益的正当性,暗示为了多数人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其个人目的,薄把“大多数人”、“老百姓”定位于按经济收入分层的社会下层,并以他们的当然代表自居,借助社会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绪,操弄他们与收入较高阶层和各级各类党政官员相对立。
红色民粹主义的反法治实质在于,它用“大多数人”是否满意的一套说辞,混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按其逻辑,为了使自己满意,“大多数人”可以让少数人牺牲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机关随时可以“大多数人”满意或“不满意”为由,非法剥夺任何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重庆红色民粹主义充斥着权力意志和高官特权意识。实际上,红色民粹主义者大搞“唱红”,本身就是宣扬出身优越、个人血统继承优势,谋求特权的表现,此举不过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的血统论的翻版。其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是“将军后裔红歌合唱团”、“开国将军后代红歌唱响中国”,张扬和显示家族身份,是要显示自己出身优越、高人一等,再结合以“唱红”形式,接班掌权舍我其谁的意味,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会看得出来。
|
||||||||||||||||||
|
Posted: 28 Oct 2012 05:05 PM PDT
1948年7月17日,储安平先生在《观察》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其中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 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
储安平批评国民政府是"拆烂污":"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
储安平的心态有着普遍性。每次想到当代几代中国精英,有谁低调了,有谁消沉了,有人移民了,有谁变脸也去"拆烂污"了……我就想到了储安平。 储安平谈到了国运。这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今天,在谈到我们大陆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时,我们都不免有无力之感。即使我们自觉还看得清楚,却难以让思想即 时生效。"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无论政权或政府为义为罪,无论个人或家族为善为恶,但在其上有着更具主宰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民族, 为上帝,为梵,为历史规律……在大陆中国,为天道,为气运。 因此,用某种学理、思潮来推导国家政权或社会的演变多会落空。我曾经乐观地预言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国人会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现在看来完全是一个笑 话。三十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现在看来只不过是狙公朝三暮四的游戏,即我说的前三十年的政治文革,后四十年的经济文革。在这样一个国家社会里上演的游戏, 幕布不落,游戏不会结束;游戏不结束,关于人性或人类社会的价值、意识形态和学理等等显得无效。 离经济文革的结束还有若干年,它以什么形态结束,我们几乎完全无法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我们都在其中分享了数额不等的"红利",甚至攫取、垄断了某种 社会资源。我们置身其中的次法西斯生活,虽然数目字管理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家为这个共同体所提供的服务却是极为卑劣的。我的朋友曾经愤激地说, 这个国家只有暴力行业和撒谎行业,除了工农等底层平民大众外,大家在这个国家只参与了两个产业:暴力产业和撒谎产业。令人发指的罪恶和苦难在我们身边发 生,我确实同意朋友的说法。精英人士、尚黑组织和驯从工具们对待异见人群、弱势人群,要么哄骗,要么镇压。 改良、改革、革命的说辞虽各有意义,但这是怎样的社会啊。我们游说不了政府,政府部门也没有谁能负责,他们上至权贵下至喝止行人的警察倒是都敢变本加厉地 行使穿了官皮之后对民众的"合法伤害权"。政权也没能把我们的人性消灭,我们仍在娱乐、上网冲浪、短信国骂。精英人士或上层也难以让它自己一以贯之,你方 唱罢我登场,粉墨人物跟文革一样可分为台上派、上台派、下台派、台下派……在现有的学理难以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和安慰之际,关于现实的讨论和未来的预测就 只能是想当然、自我感觉了。这是一个什么天道、气数或国运啊? 我在云南生活的时候,曾听到不少关于国运的说法。如推背图中的第四十四图预言了当今的国运,如有名的2012弥勒佛救世的传说,如《五公经》里面的一句断 语:"终归胡人八八秋。"据说这是指2013年国运变革。香港学者陈冠中则有小说《盛世,中国,2013》,没问过冠中兄,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五公经》。 通易变的朋友则也对我们的每一年有这样那样的判词,据说,今年的卦运是"剥"。当然,这方面的算法还有很多,比如甲子年算法,我们中国现在是国运上升时期。政权的气数未尽,是因为它跟着国运一起了。 这两年听到的预言更多。有人说国运三五年即变,这样的论调几乎年年都有听说。我的朝三暮四也算一说,很符合"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的现象,但在有些人看来就太悲观了。还有一首诗:梦惊天宇白,六四玄机开,两万五千日,忽闻近王台。 当然,还有一些立足于研究分析之上的,比如说尚黑组织的十八大是所谓的政党元年,大概是说尚黑内部分派……这似乎也对,英语词汇的政党有聚会、派对的意 思,我们的尚黑却是地道帮会性质的,如果能开始内部有派对了,也好啊。还有人想在二十大时为尚黑组织起草反毛报告,这是参照前苏联演变的作法,这当然令人 瞪目结舌。 但事实上,我并不完全认同这些对国运预言的作法。如果这些方式还有正面意义,我想除了表明对政权、世道的否定以外,就是表明言论者和听者还对某种东西有敬 畏,还多少愿意在智力上德性上有所完善……但这些有待国运变革的想法多少异化了我们,使我们三年五年,甚至三四十年或一辈子都白过了,我们没有立起来,没 有积累什么。我多次说,只要看看美国二战后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再看看我们这朝三暮四的近四十年,就明白我们在知识积累上是多么贫乏。我们可用于教训自己 教化社会的工具是不足的。 国运跟个人命运一样,在本质上仍取决于主体自身。如果把国家比做一个人,我们这个人的头脑是谁,心灵是什么?印象中,罗素先生当年曾因渺视政府罪被河蟹过 若干天,因为他劝英美政府别在遏止苏联一事上花钱,说是按他的经验,一个专制政权的寿命不会比一个人的寿命长一些,听其自然死亡的成本低得多……这也是一 种对气运的期待。但作为政权下的一分子,只能在漫漫长夜中生活,这种罪与罚该归因于谁呢? 想想十几亿中国人,在三四十年之内,政治家、实业家、思想家、仁者、志者们纷纷亮相,给过我们多少希望,如今看来一切仍是苍茫。即使我们身边的师长,在次 法西斯的游戏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流星划过,有的沉沦,有的流亡……我们有一些独立的个人,但大陆中国并不由独立的个人组成。 也许,我们立身的这个社会气数仍未尽,它仍在生成自己的拥戴者、补天者。愿得到有识之士的指教。 【余世存,湖北随州人,1969年生,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非常道》等作品。】 |
||||||||||||||||||
|
Posted: 28 Oct 2012 04:44 PM PDT
2012年9月16日,96岁胡绩伟去世了,我潸然泪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胡绩伟领导《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总书记支持下,开明办报,政绩卓著;农民喜爱,乃至拿着《人民日报》向官方维权。他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观点,被胡乔木(政治局委员)批评,被迫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我时任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秘书,见证“八九学运”戒严后,胡绩伟建议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六十年来,委员行使权力的第一人。
悼念耀邦 释放民主诉求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式,我见到深受大家爱戴的四川代表胡耀邦。11天后,他因病辞世。
4月21日晚,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露宿等待向胡耀邦遗体告别。22日,追悼大会临时由人民大会堂正门(东大门)改道北门进入,我在其中。结束后,灵车从后门(西门)驶出,前往八宝山,广大学生的要求被拒。26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起学生大游行和绝食请愿,各界上街声援,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呼唤民主与法治。
5月19日晚,我在天安门广场,十点钟高音喇叭突然播放李鹏总理宣布《戒严令》,人们震惊,愤怒责骂。随即传来,大批军车被市民拦截在六里桥等地。子夜,我到六里桥,许多军车满载的全副武装战士,被市民们围住说教并送上开水和食物,劝其撤回,而茫然不知所措。有军官登高喊道:“感谢人民的关爱,我们奉命而来,不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保证不开枪!”
危难时刻发起“紧急会议”
学潮持续一月,赵紫阳总书记反对戒严镇压而被软禁;20万大军被百万市民拦截和抗议,面临流血冲突;党政军各方处于乱局之中。危急时刻,胡绩伟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行使《宪法》赋予最高权力机关的委员们的基本权力,试图用民主与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
5月21日,北京四通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和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受胡绩伟委托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委员签名联署,来找我请顾明签名。
顾明随万里委员长出访在美国。他们说:“顾明如在,一定会支持。”我未代其签名。
接连三天,他们征集到不少委员在《建议书》签了名,11位得知此事而表示同意,达57位,超过常委会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24日,胡绩伟把联名《建议书》分送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附上亲笔信。由于万里的改革开放政绩卓著,曾发表讲话:“广大学生是爱国的。”他在国外的讲话十分开明,国内各界对他寄予厚望。
据赵紫阳回忆录(2009年香港版):“5月21日,乔石(政治局常委)来说,如不是邓小平调更多军队来京,悲剧可能避免。现在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和市民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首都将瘫痪。我(赵)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此前彭冲(副委员长)找我(赵)说,副委员长会议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真(前委员长)也赞成。”
新华社报道,万里一行将提前回国。随即,广大学生和市民环城大游行,口号有:“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万里回国,人民期待。”
25日,我到机场接顾明,却不见万里,他被留在上海。两天后,我随顾明到机场接到万里,其秘书孟晓苏说,万里在上海逗留是“正常”的。
顾明问起,听说香港报载有委员建议召开紧急会议,自己也在其中。我告知事出有因,但未签名。顾明要我查实。我打电话给曹思源,他立即赶来向顾明解释:“港报确有顾明是差误而道歉。”
胡绩伟挨整被罢官
3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华社《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声明》如下:
日前,香港文汇报和澳门日报载,有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呼吁召开紧急会议,都有高登榜、王厚德、顾明、宋汝棼。我们根本没有签名。盗用姓名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在这种严重时刻,编造谎言,混淆视听,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曾有四通研究所的人打电话给王厚德和宋汝棼,说是受某某委员的委托,希望在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书上签名,王和宋均未同意。为什么委员签名,要他们插手?为什么未经同意,竟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编造假情况?必须进一步查清,追究其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高登榜、顾明、王厚德、宋汝棼
1989年5月30日
另有李琦、刘大年两位委员发表声明被“盗用名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
随即,港报发表四通研究所声明,大意是除顾明,其他委员确有其事。报社编辑按每位委员姓名作打油词。我只记得:“顾明不明”,“厚德不德。”公布了史学家刘大年签名真迹。编者按:“作为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某委员是历史学家,应有史德,不能任意拿捏历史。”
“六四”前夜,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大卡车分兵几路,强行挺进天安门广场,广大市民把公交车横在马路作路障,扔石头,英勇抵抗,不少人被枪杀。
“六四”之后,曹思源之妻告知,曹思源、李曙光等三人在6月3日上午失踪,很焦急。我向北京市公安局资深警官老同学打听,正好他被抽调常驻秦城监狱负责预审被捕的曹思源等“暴乱分子”。
我到胡绩伟办公室拜访,胡不在,其秘书常大林在写材料,很消沉。
6月29日,全国常委会开幕,我在《简报》上看到委员们一致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批判赵紫阳,几乎人人表态,胡绩伟受到质疑被批判。没有看到胡绩伟和顾明的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通过《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根据部分委员提议,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张承先、孟连
崑
、顾明、王伟四位委员组成小组,调查胡绩伟委员征集委员签名事件。
胡绩伟专案组三次通知顾明开会,两次送来材料,注明顾明亲启,我送到顾明家。我听到专案组联络员对顾明说,正在加紧审查。我不寒而栗,深为胡绩伟捏把汗。一向坦率的顾明从未对我说什么,没要我为他整理意见,看来只是应差。
当时,我在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看到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罢免胡绩伟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决定(半年后公布,我应该不会看错)。
9月底,施滨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记者)邀我探望胡绩伟。晚上8时,我俩找到东单煤渣胡同3号胡家,悄然绕到后门,隔窗看到胡老,推门闯入。得知我是顾明的秘书,胡老惊恐,我赶紧欠身鞠躬,以示敬仰,他放心了。
我说,顾明过去曾说:“历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从不整人。”我俩问了胡老一些家常,不便久留而告辞。我感受到胡老内心镇静,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后两月,胡绩伟专案组未通知开会,未见结案报告。
另据悉,胡绩伟案的事实查清后,三位正副委员长均认为胡绩伟是正当履行委员职责,不能视为非法或违纪,不予处分。
1990年3月,胡绩伟突然被四川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分别撤销其代表和委员职务;原单位人民日报社党委,做出开除其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央,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常大林被调《博览群书》杂志。数年后,他对我说:“胡老深入反思,不断在港刊发文,还撰文百万字,自编自印《文选》数集。”
胡绩伟的反思与呐喊
胡绩伟撰文:“八九民运”被镇压,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席卷全国,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代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以党代政,包办和决定一切,人代会成了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变成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北京发生大屠杀,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制,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胡文指出:赵紫阳是正确的,罢免其总书记职务违反党章,被软禁被监控违反党纪国法。胡耀邦为党为国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被邓小平“逼宫”而下台,邓是历史的罪人,胡冤案应平反。
胡绩伟精神感召我为民办实事
胡绩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精神是我的楷模,后来我尝试用宪政之法为弱势群体维权做了两件实事成先例,受到垂暮之年顾明的热情鼓励。
2002年初,国务院新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把所有的单位和个人在未经授权的非商业合理使用软件,定为非法并处高额罚款而成恶法,百姓反响强烈。“两会”期间,我参与游说代表、委员,60多位分别向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交《议案》和《提案》,要求修改条例。年底,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把软件保护限制在商业使用范围内,极大的缩小了打击面。
2004年初,河北省四万水库移民款被当局挪用,上访8年未果。“两会”前夕,我参与指导移民们提出罢免该市党政领导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征集了一万三千失地农民签名联署,代其呈送全国人大会议秘书处和吴邦国委员长,虽未被理睬,但“万民折”震动了地方领导,而对访民改打压为安抚和慰问,用五亿元解决了常年大规模群体性上访问题。
胡绩伟在位时主持起草“新闻法”,下台后一直呼吁翻案“六四”,上书要求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言论和出版自由”(笔者参与签名)等,直至去世,仍未实现。
两年来,中共体制内呼吁政改的开明智者朱厚泽、李普、谢韬等相继辞世,历史的重任正向吾辈袭来。
(于2012年10月26日修订)
胡绩伟:九十五大寿赋诗:
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
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
远闻茉莉吐艳,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
壮哉,寿追南山!
曹思源:悼绩伟
拔乱反正泽天下,
九旬思想更升华。
忘年之交缘何结?
一根藤上两"苦瓜"。
历史正邪终能辨,
宪政大道乐无涯 !
于浩成:敬悼胡绩伟挽联
胡公千古
党报总编辑,宣扬政治改革,主持起草新闻法,保障言论自由,无私无畏;
人大常委员,支持民主抗争,呼吁废止戒严令,抵制镇压行动,功败垂成。
——于浩成敬挽2012年9月17日
胡绩伟简历:胡绩伟,四川威远人,1916年生,1937年加入中共,先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因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一事被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
============================
本文写作轶事:
9月上旬,得知76岁张显扬先生(中国社科院原马列所研究员)病危“弥留之际”,我悲痛之极,深感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之大,难以割舍。告知《动向》杂志张伟国先生,他约我写悼念文。我含泪回首1985年认识他以来,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亦师亦友的往事,历历在目。不料,胡绩伟去世,打断我的思绪,而含泪先写悼胡文。后见孙长江说,张显扬的生命仍在维持,有可能好转,先不忙准备后事。我很欣慰,未撰悼张文。10月11日,张老师奇迹般地出院了。张老师才华横溢,有着许多未尽的历史使命,抑或是胡绩伟抢先离去,而保佑晚辈同道张显扬,要活到奋斗到胡绩伟的年纪乎!
梅荪兄:
可能是你要写悼张文“冲”了一下死神。我国汉族文化传统中有“冲”一说。人若有去世的可能,为其提前准备后事,有可能把“去世”冲掉,这在《红楼梦》中有例子。还有用结婚之喜事来“冲”的。
这几年间,曾当面给我指导的谢韬、朱厚泽、李普前辈相继去世。在他们走向生命终点的过程中,我都疏于问候。我专心做与他们有继承性的理论事业,使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所以我原谅自己的顾此失彼。向张显扬老师问候,他除了有思想有原则外,还是个大帅哥呢!要长命百岁才行!我期待继续得到张老师的指点批评。
——刘利华,10月11日
小俞:
谢谢你的这篇宝贵的历史记录纪念文。
——胡雪滔(胡绩伟之女)10月13日
●原载《动向》2012年10月号,初稿2000字。
●首发《纵览中国》2012年10月28日,修订为4800字文。
作者供稿
|
||||||||||||||||||
|
Posted: 28 Oct 2012 04:53 PM PDT
俞家三代"一滴泪",滴出赤潮入华后的"绩效",一张所谓"最新最美"的蓝图非但未泽被后人,反而肇祸连连,绵延至今。俞家三代的人生轨迹提供了一份十分独特且极其珍贵的家族标本。
祖迎马列
我认识俞梅荪先生乃是从其祖父开始。其祖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明代抗倭总兵俞大猷(戚继光为副总兵)之后,中国最早迎请马列主义人士之一。1920年10月,由张东荪、梁启超促成,俞颂华作为京沪两大名报(《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赴俄,瞿秋白仅为其所雇译员,另一俄专生李仲武自费随行。采访过列宁、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赤俄领导人,并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供给制(三月免费食宿)。因当时赤俄全国挨饿,俞瞿李有时也挨饿。这一期间,俞颂华连续发回报道,与瞿秋白一起将马列主义"贩运"回华。
其后,俞颂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4月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人,发表长篇报导。
1924至1949年,俞家经常为瞿秋白(1935年被杀)、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秘护家中。其学生有范长江、石西民、陆怡、沈昌焕(国府外长)、郑心永、傅白芦、王淮冰、方汉奇等不少国共精英。抗战后国共内战,俞颂华上了国民党暗杀黑名单。
俞颂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不远万里"贩运"回华的这个"主义",非但没有长宜子孙、泽被后人,反而肇祸连连,其子其孙竟成为直接受害者。三代俞家人,一滴辛酸泪,一滴那么伤痛滞坠的世纪国泪!
子死五七
第二代,独子俞彪文(1926~1957),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生,1949年拒随国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
讬
局赴台,参加中共开国大典,创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办公厅副主任,得财政部长李先念好评。因对保险工作提出一些改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57年7月19日,在"伟大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跳楼自杀(最早自杀"右派"),年仅31岁。
俞彪文"与人民对抗到底",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业务骨干的母亲(1949年参与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资减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妻子(重庆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马寅初学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97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到俞家宣布"改正":"你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为怀就不算了。"民政局按1957年标准放发抚恤金(安葬费)360元,若按1979年标准应为1500元。这就是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①
2003年,俞彪文妻临终前告诉两儿:她当时想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实不忍抛下四岁和一岁幼儿,坚强活下来。"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与蒙冤入狱。我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太没意思。"
孙陷冤困
第三代,长孙俞梅荪(1953生)、幼孙俞颂荪(1956生)从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文革"在沪屡受冲击。幼孙颂荪中学毕业时三次自杀, 一次触电、一次割腕、一次喝敌敌畏,最后一次因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哥哥梅荪在家,立即灌水洗胃,再送长宁区中心医院抢救,差一点"呜呼"。颂荪精神抑郁,有时要住精神病院。他居住的俞家祖宅(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3层42平米廉租公房),被长宁区政协委员惠进德(俞梅荪江西插友)构陷侵吞,官司一拖五年,要回到俞宅居住,征途漫漫。去年,这所尚在争讼中的该屋被市府列为"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
俞梅荪1979年入党,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长(1985年起草《"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之秘书,著有《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十多家报刊转载,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1988年正处级秘书,1991年副研,北大法律系兼职副教授,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1992年9月,出于纯良动机,按惯例向专程来京的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出示《"十四大"征求意见稿》,以便其搞好法治宣传。因一时疏忽,文件被盗印,再牵扯到一笔与本案无关的两千元资料费,1994年1月,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之罪逮捕。
尽管泄密产生良好的正面效果,江平大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出庭作无罪辩护,首长顾明伸手相援,但仍判刑三年,俞梅荪一生就此被毁。在狱中,俞任班长、教员,全班月月超额完成劳改指标,成为全监狱劳改积极分子,本可减刑一年,因拒不认罪,坐满三年。1997年1月出狱,仍因不认罪,片警"依法"不让申请低保,且各方推诿,不解决其生存问题。应聘求职,屡因"刑释人员"遭拒。如今岁垂六旬,生存无着,妻离子散。为照顾弟弟和要回到俞家祖宅(俞颂荪惟一居所)住宿,四处奔告,依法维权上访,不是遭拒就是被骗。
1994年,因兄长入狱,其弟受惊吓,精神病复发,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如今,因俞宅被人侵吞,无家可归,颂荪滞留精神病院已12年矣。其间多次自杀被抢救,电击休克治疗使其丧失记忆。2008年初,颂荪病愈出院回俞宅被赶出,2009年初上访,因到处被拒,是年8月再次要自杀,旧病再发,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送回医院成危重特护病人。在精神病院内多次撞墙自杀,电休克治疗,惨不忍睹。五年来,参与立法10年的俞梅荪,竟也沦为求告无门的访民,落难江湖,底层挣扎,常年流浪于沪,深陷困境。俞家兄弟,真正的"当代不幸者"。
绝望法律
俞梅荪遭《文汇报》团伙作案人栽赃陷害,十分愤怒,深感司法不公。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诉庭副庭长纪敏,前往探监。俞告知:"江平为我无罪辩护。"纪副庭长回答:"律师算什么?关键要看法官的。" ②随口一语,抖尽律师在中国司法中的地位。2009年9月底,北京大学几位法学教授、维权律师拟定以俞宅侵吞案为例召开"上访个案研讨会",讨论结果将通报国家信访局,校方已批准,京沪法治报刊不少记者报名参加。然警方以"六十大庆"维稳为由,强令取消研讨会,并将俞梅荪"限居"在家一个月。
出狱16年来,俞梅荪发表法治建设文章数十篇,得到江平及老首长顾明称赞。多年来,因替失地农民维权上访、不断参加"右派"维权聚会、每年老领导赵紫阳忌日到赵家缅怀,他成了警方"重点保护对象",家门口一度探头伺候(探架犹在),"敏感时期"警员全天候陪住。俞见警员大冬天瑟索于传达室,迎入家门食宿,方便警员"执行公务",尽管有时与警方对抗激烈。俞梅荪有时外出,一刷身份证,蹦出"重要信息",警方立即紧张起来,"有关方面"会迅速赶到。一次,自沪回京,刚到家,北京警员就上门"问候",生怕他"途中消失"。
2010年1月23日,北京《律师文摘》杂志举办"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首发式"(编入俞文《江平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江平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法律系,大陆法律界泰斗,发表演讲《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几位警察了解俞家冤案后:"你这搞立法的人都被冤枉得如此凄惨,老百姓怎么办啊?你落难又遭欺诈,房子被人侵吞,这种事太多了,你还能说能写,但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法,无处说理,只好自认倒霉了。"③
2012年4月8日,本人首晤在上海流浪的俞梅荪先生,亲感他走投无路的激愤。在座四人临时凑捐两千元。另一聚会,一读者亦捐两千元。俞先生很尴尬,不收拂逆好意,收下又深感不安,但他确实需要帮助。将这样一位红色出身的党员高知"培养"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汉,一位本可为国尽力的栋梁之才,沦为求告无门的弱势访民,一次次领受唾面自干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而产生与仇家同归于尽的杨佳式冲动。他现在特别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访办大铁门外的访民,"个个艰苦卓绝,比我艰难困苦得多。我沦为访民,才真正理解他们的苦大仇深和万般无奈。"
泪痕难干
俞家三代"一滴泪",多么凝重哀伤的一滴国泪!更使我感叹的是:以俞梅荪的精通法律和如此广泛的人脉尚不能为自己的两桩冤案依法维权,这个社会的弊病应该相当"深化"了,至少纠错力量太弱,法律远远未能起到扶弱矫谬之力。俞梅荪深感公平立法固然重要,但当今大陆首在公正执法。"那些执法者并不执法,甚至是反执法。"
俞家三代的血泪,默默述说着赤潮入华后的"绩效"。唐士军律师说:"六十年中国,究竟是什么社会?简直是东亚地狱!"话虽黑色,但一个至今仍奉专政为圭臬的国家,又怎么会允许法律干扰"和谐"?没有意识形态的正位,现代人文理念均无法具体落实。从这一意义上,俞家三代为国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独特且极其珍贵的人文标本:祖迎、子死、孙冤!
最有反讽的是:官方设立"俞颂华新闻奖",俞家后人,竟然至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国人今天还不能反思一下形成这一悖谬的原因么?
只能搭乘马列号驶入"历史三峡",直流而下63年,乃20世纪中国的宿命。无论如何,中国大陆的现状,直接来自"光芒万丈"的指导思想――马列赤潮。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实践已经检验了,那么"真理"呢?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每艰难挪走一步,最强大的阻力均来自意识形态,真正思想"长"一寸,生产才能向前进。赵紫阳晚年感叹:"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
(2012年10月于沪)
注释:
①俞梅荪:《缅怀蒙冤自杀的右派父亲》,载《开放》2008年9月号。
②③俞梅荪:《江平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原载《前哨》2010年2月号;原载《江平八十华诞庆贺文集》(2010年1月北京版)
●本文简版1900字,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9月号
●纵览中国,20120917,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615
——俞梅荪供稿
|
||||||||||||||||||
|
严家祺:从温家宝家族巨额财产看制定《国家政务官家族财产法》的必要 Posted: 28 Oct 2012 04:55 PM PDT
《纽约时报》昨天公布了温家宝家族利用温家宝的权力和影响力聚敛了二十七亿美元的巨额财产的消息,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大清王朝出了一个和绅,今天中共王朝出了一个家宝。和绅当政二十年,皇位更迭,和绅到了霉。在嘉庆皇帝初被抄家,和绅的财富估计有十亿两白银。嘉庆皇帝没有把和绅的财富区分为"和绅老婆"、"和绅儿子"、"和绅九十岁母亲"、"和绅弟弟"的,反正一下子就把和绅端了出来。今天,中共王朝正在发生"皇位更迭",家宝想到他的老前辈和绅也惶惶不可终日。
今天的中国应当努力扫除"王朝"残余,使"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首先应当确立"宪法至上"原则、限制党和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如实行党政分开、不能用宪法上没有规定的"政法委书记"独揽司法大权、使公检法相互制衡。国家官员或公务员,应区分为"政务官"和"文官"。"文官"是一般"国家公务员",按《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任命,他们不需要"拍马屁",不怕得罪"上级",实行"无过失不得免职"的原则,有良好的待遇和退休保障,是"铁饭碗",一旦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权渎职,法律应规定取消他的一切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而"政务官"实行与"国家主席、总理同步更迭"原则,制定《利益冲突法》、《国家政务官家族财产法》,防止"温家族敛财"现象的发生。
在现代许多法治完善的国家,利用权力聚敛巨额财富的事,是很少发生了。全国人大有必要把这些国家的有关法律一一加以研究,制定出中国的《制止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的各种法律,包括《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等。
在资本全球迅速流动的今天,有两种办法可以在短期内攫取巨额财富。一是利用国家权力、二是利用金融漏洞和金融欺诈。今天的中国正在开放资本市场,这两种方法可以同时并举。路透社记者约翰・弗利(John Foley) 说,外国的许多投资者都是对拥有政治靠山的企业进行投资。因知道内情,私人股分公司和西方投资银行通过上市前投资的手法就可以赚取几十亿美金。所以一点都不需要对联合国资料表示惊讶:中国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在2012年前半年就吸引了590亿美金。"温家宝家族"的巨额财富,是在今天中国金融体制存在大量漏洞和金融法规不完善的条件下、在全球资本迅速流动的条件下,利用高官权力和影响力而取得的。温家宝任总理十年,使中国的以权谋私和金融欺诈现象泛滥成灾,在这一点上,他的总理也没有当好。
(写于2012-10-25)
|
||||||||||||||||||
|
我的中国梦――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Posted: 28 Oct 2012 04:57 PM PDT 你们好。
贵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贵党目前是中国的执政党,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者,你们的党代会不仅仅是贵党的内部事务,还将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不想总是“被政治”或者被代表,我们有话要对你们说。
从建党时起,到最终取得政权,贵党曾一再宣称,贵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贵党的公开承诺,曾激起无数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与热望。在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上,人们就曾读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宣言:“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在选举以前,要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 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
但是,在贵党执政六十多年后,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中国人的政治命运依旧被少数人在密室里决定着。
六十多年来,贵党一直垄断国家政治权力,无视人们希望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当要求,拒不开放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中国人一直无法享有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始终生活得缺乏自由和尊严。
六十多年来,法律一直是任由权力随意掐捏的橡皮泥,各级政府及官员经常公然违背自己一手制定的法律,司法机关没有成为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反而成了政府肆意侵犯民权的马前卒,甚至沦为政治官员任意差遣的家丁和打手。
六十多年来,政治权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权力腐败几乎已遍及所有的公共领域,严重的政治腐败不但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使整个社会风纪败坏、公义不彰。
六十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不是用于提高民众的福利,而是用于各种极尽奢靡的公务消费,有限的社会保障资源,不是用于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而是用于为各级政府官员提供过于优厚的待遇。
六十多年来,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及信仰自由,不是被彻底剥夺,就是被施加严苛的限制,人们无法自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国家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无法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国社会一直难以走出理智蒙昧、道德沉沦的可悲境地。
各位代表,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这种不公正和不正常的状态,最主要、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政治制度不民主,政治权力太集中。我们给你们写信,是想敦促你们履行贵党迟迟未能履行的承诺,摒弃一己一党之私,展现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做出正确和有远见的历史抉择,将贵党从我们手中剥夺的各项政治和社会权利,一一还给我们。
我们要求得到这些权利,是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在政治上失去了这些看似抽象的权利,我们一直都在生活中品尝着各种具体的苦果。
我们周边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我们开始看不到明媚的蓝天,找不到清澈的河流,喝不上干净的饮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
我们的药品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我们的药品有时不但不能医治我们的疾病,反而还可能夺去我们的性命;我们每天都可能食用有害的食品,连我们的婴儿也经常被有毒的奶粉戕害。
我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新建的大桥随时都可能坍塌,人们甚至有可能在天降大雨的时候,悲惨地溺毙在首都城市的主干道上。
我们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很多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有些人不但要肩负生活的重负,而且还要日夜躲避城管的骚扰和追逐。
我们时刻都在忍受权力的欺凌和压迫,我们的房屋不断地被政府强拆,我们的钱财不断地被政府掠夺,我们中不断地有无辜的人被囚禁、被失踪、被自杀。
各位代表,我们有必要坦诚地告诉你们,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社会弊病,让我们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意。贵党作为国家权力的垄断者,对各种社会弊病的发生,负有首要和重大的责任。
但我们向你们写信,并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愤怒和怨恨,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要求和希望。各位代表,我们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你们的良知会被私利所蒙蔽;不相信你们的理性会被权欲所压倒;更不相信奴役和动荡的轮回,是中国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各位代表,我们希望你们能正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这些问题使得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分裂日益突显,并使中国的社会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社会稳定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各位代表,你们经常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要想社会稳定,就必须正视和解决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必须改变使各种问题不断滋生的政治权力结构。
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就一日都得不到安宁。近年来,从乐清到乌坎,从什邡到启东,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争,已经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和积蓄。
各位代表,已经到了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时候,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为了避免中国再次陷入动荡的深渊,你们该做的不是挥舞维稳的大棒,而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倾听民众的心声。
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我们最坚固的建筑是孩子们在其中学习和玩耍的校舍,而不只是雄伟壮观、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不必以下跪、自残甚至自杀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安身立命的住宅,更不会在保护住宅的过程中,被推土机残忍地碾压,被枪弹无情地射杀。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既能有接受各种教育的平等资格,也能有担任各种公职的公平机会;一个人是否有机会升学或任职,将完全取决于他的才干和品德,而不是他的背景和关系。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自由地谈论公共事务,自由地批评政府及官员,而不用担心被无处不在的网警监控,更不用担心因为触怒权力而被劳教、被判刑。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有一天,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公正的选举中,一人一票举出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政府的各项决策也都尽可能公开透明,政府官员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在民众面前都是尽职、热情和谦卑的公仆,而不是失责、冷漠和傲慢的权贵。
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从一片不公和不义的荆棘之地,变为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祥和之邦。
各位代表,这就是我们的心声,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这也可能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的梦想。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早日实现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的自由、安全、幸福和尊严,不但与中国的进步息息相关,而且彼此也紧密相连。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不能平等地分享自己国家的政治权力,那么少数独握大权的人,也不可能感到丝毫的安全。因为在不公的怒海中,不可能存在安全的孤岛。
各位代表,我们的国家已历经了几千年奴役、专制和不公的厄运,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因此一直遭受着连绵和深重的苦难。但我们相信,一个国家越是长时间受困于奴役、专制和不公的黑夜,就越有理由期盼自由、民主和公正的黎明。
各位代表,我们带着善意给你们写信,并希望能从你们那里得到同样善意的回应。我们向你们坦陈我们的中国梦,是希望你们成为我们追求梦想的同行者,而不是我们实现梦想的阻碍者。
各位代表,比权柄更有力量的是民心,而你们应该清楚民心所向。当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安逸富足的中产阶级,追寻法治秩序的法律人,不愿放弃新闻理想的媒体人,反对政治洗脑的教师,崇尚自由平等的知识分子,珍惜职业荣誉的警察和军人,都开始发声,都要求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梦,你们应该知道闭目塞听,一意孤行,或者干脆把异议者送进监狱,决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你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释放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内的一切良心犯,营造宽容互信的社会氛围,让中国梦生根,让中国梦生长。
各位代表,你们将做出你们的选择,而由无数怀有梦想的普通公民构成的我们,将做出我们的选择。
我们不仅是做梦者,我们还是造梦者,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手里实现梦想。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就是总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下一代。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怠惰和自私,给我们的后代遗留一个巨大的隐患,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奋斗和付出,给他们留下一份宝贵的资产。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宪政中国,就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孩子的最好礼物。
顺致秋安。
中国公民
2012年秋
附:一个呼请:
所有认同本文本主旨的中国人,请帮助传播这份公开信,请以你们各具创意的方式,来阐述我们的中国梦。
|
||||||||||||||||||
|
Posted: 26 Oct 2012 12:25 PM PDT
原题:“入常”的寡头交易规则2012-10-26
十八大在即,境外的媒体提出的新常委名单五花八门,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现任适龄政治局委员。其实,不仅是境外媒体对这个五年(或者十年)一度的“新常委猜谜”的游戏乐此不疲,包括近四百位中国执政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的中国政治精英们目前也都在焦急地等待著谜底。
这一现像表明,政治规则的不透明和政治前途的不确定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也是对那些声称中国在政治继承问题上已经实现了制度化、程序化的中、外政治学者的一个嘲弄。当然,缺乏透明的规则不等于没有规则,但是它是一种没有法律准则的潜规则。这种人治的潜规则并非始自今日,在毛泽东时代便已经存在。
在独裁者的治下,这种潜规则的核心就是独裁者的意志。由于独裁者的意志是变化的,因此规则也在变化。毛泽东废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邓小平废黜胡耀邦、赵紫阳等就是变化无常的独裁规则的体现。现在的中国,没有人具有当独裁者的实力了,开始盛行一种新的潜规则,就是“寡头交易”规则。政治接班人成了极少数政治寡头的幕后交易品。 了解遴选政治接班人的寡头规则是理解中国现行政治生态的一部分,它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的决策程序,从而比较“靠谱”地预测中国政治精英集团成员的政治行为及其政治和社会后果。在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的遴选过程中,这种寡头规则包括那些内容呢? 首先,任何希望能够入常的候选人都必须是具有决定权的寡头所能够接受的人物。由于没有了绝对的权威,所以这极少数寡头各个都有否决权,假如你得罪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的政治前途绝对终止,搞得不好你的结局还会身败名裂。薄熙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有人认为薄熙来是因为到重庆后奉行一条别出心裁的路线和政策才导致目前的结局的。持这种看法的人只知其表,不知其里。薄熙来注定出局是因为胡锦涛早在五年前就开始布局对他行使否决权。五年前的薄熙来,既有地方党政主要首长的经历(大连市委书记和辽宁省长),又有中央重要经济部门的首长经历(商贸部长),应该是政治局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首要人选,假如当时他沿著这条路径走下去,在十八大前的“入常”的竞争中便会成为尾大不掉的领跑者。 胡锦涛当时便为今天行使了最终的否决权作出了铺垫,将薄赶出了京城。因为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是胡锦涛和整个团派出身的干部的政治敌人。薄一波依仗邓小平授予的权力,在代表老人党清理改革领袖胡耀邦的过程中试图将凡是与胡耀邦有干系的人一网打尽,其中就包括胡锦涛、王兆国、刘延东等人。有了这种渊源,薄熙来无论如何是不会成为胡锦涛的政治盟友的。作为具有否决权的最终要的政治寡头之一,胡锦涛行使否决权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 其实薄熙来对此也心知肚明。可是他不是一个“认命”的主儿,还寄希望于另辟蹊径,在出局后重新入局。他在重庆的路线,虽然与胡锦涛的“亲民政治”和“毛泽东主义”并无根本不同,却得罪了江泽民,因为他所批判的正是江泽民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政策。于是,作为另一个政治寡头,将也行使了否决权。这就注定了薄在政治上不仅“死定了”,而且还会死得非常难看。 “入常”的第二个规则是在半公开的帮派竞争中得到帮主的绝对信任。只有这样,帮主在与其他的政治寡头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才不至于将你作为权力交换过程的牺牲品。但是,假如做得过火,锋芒毕露,便违反了规则一,很容易让其他的帮主行使否决权;假如做得火候不够,在本帮帮主的心目中又缺乏分量。在寡头支配政治权力的帮派角逐中,要取得这样的平衡要花费很多的功夫。 第三个规则是中庸规则。由于要避免遭受政治寡头的否决,所有的候选人都要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尽可能地表现中庸,藏头藏脚,让人找不到任何破绽。他们必须说千篇一律的话,做不得罪人的事,让任何人都感到对自己没有威胁。 久而久之, 他们可能在“入常”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但是却在制度创新的政治能力上一步一步后退。 第四个规则就是以年龄划线和论资排辈的规则。由于谁都没有政绩,也由于每一个政治寡头都有否决权,除了极个别人之外,大多数只有靠以年龄划线和论资排辈了。例如,在有适龄的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已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委员比担任地方大员的委员们有优势。已经担任了两届政治局委员的比只担任了一届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刘云山、张德江、王岐山、俞振声、李源潮等人具有相对优势。 按照这四个“潜规则”来进行十八大常委的猜谜,大致可以八九不离十。问题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进入常委的人,很难为成为具有领袖气质的政治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缺乏合格的政治领袖,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会使得当今的世界更加缺乏稳定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26 Oct 2012 12:47 PM PDT
更新时间 2012年10月2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01
|
||||||||||||||||||
|
Posted: 26 Oct 2012 12:17 PM PDT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 1959年流亡印度的達賴喇麻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國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國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產黨”、“热爱社會主義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陆肆”流亡的中國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國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達賴喇麻,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鄧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鄧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國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黨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國共產黨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國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 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國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國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國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國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 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薩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國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達賴喇麻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達賴喇麻的尊称。祝福達賴喇麻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國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薩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達賴喇麻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達賴喇麻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達賴喇麻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 “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達賴喇麻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達賴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達賴。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達賴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 “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達賴喇麻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達賴喇麻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達賴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華圈。有的人长期受到黨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國共產黨、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達賴喇麻。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鎮壓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達賴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達賴喇麻的敌对。達賴喇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達賴世系和達賴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達賴为敌,就等于与全部達賴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達賴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達賴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達賴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9而達賴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達賴喇麻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薩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鎮壓,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達賴喇麻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達賴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達賴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達賴喇麻。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薩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達賴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達賴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薩‘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 達賴喇麻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達賴顶礼膜拜,達賴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達賴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達賴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達賴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1995年達賴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達賴定性:
“達賴是图谋西藏獨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華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達賴喇麻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達賴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達賴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達賴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達賴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獨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薩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達賴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達賴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達賴的操纵下拖出来”15,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黨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達賴;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黨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黨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達賴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達賴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黨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黨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 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
“宗教与社會主義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達賴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會主義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黨的饭就得听黨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會主義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鄧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達賴喇麻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達賴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麻”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達賴喇麻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達賴喇麻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達賴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達賴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達賴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達賴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達賴,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達賴喇麻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達賴和以前的達賴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達賴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達賴喇麻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達賴喇麻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達賴喇麻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達賴,以及逼迫藏人对達賴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達賴喇麻汇报,最终使達賴喇麻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達賴喇麻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黨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達賴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達賴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產黨,来世靠達賴喇麻”,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產黨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達賴喇麻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達賴。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達賴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達賴喇麻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達賴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達賴喇麻。至于在普通居民家,達賴喇麻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達賴喇麻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 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達賴,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纹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達賴喇麻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黨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權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國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達賴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國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國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達賴,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達賴,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國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達賴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達賴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國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國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國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國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 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國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國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達賴喇麻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國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權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國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達賴喇麻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達賴喇麻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國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獨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國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國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獨立。
不要说中國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 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獨立的界限,抢在中國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國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國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國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國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國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達賴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國,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國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獨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國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國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國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國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達賴喇麻今年65 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國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達賴喇麻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獨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獨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國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麻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達賴喇麻,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國”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國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達賴喇麻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獨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獨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達賴喇麻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達賴喇麻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達賴喇麻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達賴喇麻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達賴喇麻,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達賴喇麻,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達賴喇麻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達賴。那时北京所立的達賴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達賴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達賴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國、坚持西藏獨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獨立,就是達賴喇麻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達賴喇麻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達賴喇麻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達賴喇麻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達賴喇麻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國与十四世達賴喇麻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達賴喇麻,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國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國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達賴喇麻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獨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國怎么办?
因此从中國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達賴喇麻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達賴喇麻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達賴是不利的,对中國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達賴喇麻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國反達賴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達賴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 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達賴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達賴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達賴的宗教外衣”32,然而達賴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達賴喇麻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達賴去世后另立一个達賴,也不会达到目的。達賴喇麻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國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達賴,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達賴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達賴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達賴喇麻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產黨人,尽可以把達賴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黨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達賴喇麻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達賴喇麻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達賴打开过大门,是達賴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達賴喇麻。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達賴喇麻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達賴喇麻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達賴喇麻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達賴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國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麻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麻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麻提出的标准是——“中國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國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麻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國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國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國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國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國与達賴喇麻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从而可以“让中國人放心”的保有中國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國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獨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2000年5月 初稿于拉薩
7月 定稿于北京
注释:
1 斯塔,《江澤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國西藏1998年3期。
2 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黨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页99.
4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页99.
5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页31、99.
6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國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gov.cn/ ).
7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國统计出版社,页16.
8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 时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達賴喇麻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黨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0 安七一,《達賴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國西藏》1999年3期。
11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 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黨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 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 按照達賴喇麻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達賴喇麻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薩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发表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道《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達賴绝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國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 《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9811
26 见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http://www.tibet.com .
27 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导,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1507亿美元(高于中國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28 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议》,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1959年的拉薩事件和達賴出走,已经导致协议从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29 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達賴喇麻?》
30 達賴,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薩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1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3 達賴喇麻,1997年5月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
34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薩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5 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薩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6 台湾《中國时报》記者林照真,《獨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37 達賴,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薩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
中国观察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纽约时报: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中国――安全感缺失加速“用脚投票”浪潮
- 刘云会客室:程翔谈社科院香港报告
- 晴朗:大陆反日,香港反“国教”
-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在港首发
- 朱毅:蓝哈达,金哈达――荔蕻大姐的五七华诞纪实
- 金钟:十八大徘徊歧路
|
纽约时报: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中国――安全感缺失加速“用脚投票”浪潮 Posted: 01 Nov 2012 11:17 PM PDT IAN JOHNSON 报道 2012年11月02日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陈括,30岁,动身前往澳大利亚前在北京的寓所。
北京——今年30岁的陈括曾拥有很多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一些东西:一套属于自己的单元房和一份跨国公司的高薪工作。但10月中旬的一个午夜,她却登机飞往澳大利亚,去那里开始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就像每年离开的数十万中国人一样,驱使她离开的是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在国外会过得更好。尽管中国最近几年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她还是向往澳大利亚,因为那里可以提供更健康的环境和完善的社会服务,还可以提供在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国度建立新家的自由。

对中国移民来说,美国是一个受欢迎的目的地。
“中国太压抑了——有时候,我一周要在上班的那家审计公司工作128个小时,”离开前几个小时,陈括在她北京的房子里说。“而且,在国外养育信仰基督教的孩子会更容易一点。澳大利亚更自由一些。”
中国共产党正在为11月初的领导人大换届做准备,与此同时,像陈括这样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流失。最新完整数据显示,2010年有50.8万中国人离开中国,去了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人数比2000年增长了45%。
单个国家的记录显示这个趋势还在继续。2011年,美国接收了8.7万来自中国的永久居民,一年前的数字则是7万。中国移民使得从曼哈顿中城到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的一系列大相径庭的地方房价攀升。曼哈顿的一些房地产中介正在学习普通话,而塞浦路斯则提供获取欧盟护照的途径。
很少有中国移民把政治作为离开的理由,这样的沉默却凸显了他们的许多担忧。他们说不计任何代价搞发展的战略已经毁掉了环境,堕落的社会和道德体系也让中国变得比他们小时候还要让人感到冷漠。总之,他们有一种这样的情绪:尽管中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它的政治和社会走向仍然很不明确。
“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未来,特别是子女的未来没有安全感,”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研究中国移民的副教授曹聪称。“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环境不稳定。”
看起来,大多数移民都只是把外国护照当做应对最坏情况的一种保险,并不想彻底抛弃中国。
上海一家工程公司的经理在匿名的条件下称,他今年早些时候在纽约市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上投了资,希望最终能拿到绿卡。他还是一个言辞犀利的时事评论博主。他说,当地公安人员找他谈过话,致使他获取美国护照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
“绿卡是一种安全感,”这位经理称。“这里的体制不稳定,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倒想看看,下面几年这里会变成什么样。”
政治动荡也加重了这种情绪。今年初,共产党高官薄熙来的丑闻曝光,震惊了全国。根据官方报道,他的辖区竟然充斥着谋杀、拷打以及腐败活动。
“哪怕是在最高层,哪怕到了薄熙来的级别,仍然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和风险,”奥尔巴尼大学(University at Albany)移民问题专家梁在称。“人们不知道两三年后会发生什么。”
不安全的感觉也影响到了那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差的中国人。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去年年底有80万中国人在国外工作,1990年的数字则只有6万。很多人都在做小生意——开出租车、捕鱼或者种地——还担心自己这个阶层错过了中国的30年繁荣期。尽管在此期间,中国有上亿人脱离了贫穷的生活,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经济也越来越被大公司主导,这些大公司很多都是国有企业。
“这种潮流的动因是害怕在中国成为输家,”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人口学家项彪称。“出国已经成了一种或许能带来一些机会的赌博。”
在海滨城市温州经营一家餐馆的张林(音译)便是这样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所在的大家庭里的农民和生意人把钱凑在一起,送他儿子去加拿大的温哥华读高中。家里人希望他能进入一所加拿大的大学,将来的某个时候能获得永久居留权,说不定还能让他们家所有人都移民过去。“这就像一把椅子,椅子腿不止一条,”张林说。“我们希望在加拿大安放一条腿,以防这儿的这条腿折了。”
如今,移居国外的形势已不同于过去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学生开始出国,其中许多都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留在了西方国家,因为那些国家主动为他们提供居留权。上世纪90年代,没钱的中国移民付钱让“蛇头”把自己带到西方去。他们有时会搭乘货船,比如1993年在纽约市搁浅的“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这一现象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如今,多年的繁荣意味着数百万人具备了合法移民出国的途径,要么通过投资项目,要么通过送子女出国留学,寄希望于获得一个长远的立足点。
北京一家传媒公司的秘书王瑞金(音译)表示,自己和丈夫正在劝说23岁的女儿申请新西兰的研究生院,希望女儿能留在那里,为家里人打开出国的大门。她说,自己和丈夫都觉得女儿拿不到奖学金,因此家里人正在借钱,就像是做长期投资。
“我们感觉,中国不适合像我们这样的人,”她说。“想在这里取得成功的话,你要么得堕落,要么就得有关系。我们更喜欢过稳定的生活。”
这个话题已经在官方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这或许表明了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方竹兰在半官方杂志《人民论坛》上撰文说许多人是在“用脚投票”,还把大规模移民出国现象称为“民营企业家们对自身权利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保护和实现程度的消极评价”。
这股潮流并不完全是单向的。鉴于西方各经济体趋于停滞,就业机会受到限制,2011年归国的学生人数较前一年增加了40%。政府也设立了一些高调的项目,通过暂时提供各种额外待遇和特权来吸引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回国。然而,诺丁汉大学的曹聪教授表示,这些项目取得的成果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
他说,“归国人员都能想到,五年之后,他们也将变成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处境和那些已经在国内的同事一样糟。这就意味着,很少有人会被吸引回来长期居留。”
许多移民问题专家表示,这些数字和其他一些国家过去的经历是一致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和韩国都有过人口大量流向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历,尽管当时它们的经济正在起飞。财富和更好的教育让人们有了更多移民出国的机会,那时的许多台湾人和韩国人之所以出国,部分是因为担心受到政治打压,就和现在的中国人一样。
尽管那些国家最终都走向了繁荣,迎来了开放社会,但许多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却是,幕后选定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下一届领导班子派系林立,是否能够带领中国进入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在这里很兴奋,但又对未来的发展感到很迷惑,”去年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获得硕士学位的彭磊说。如今,他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名为Ivy Magna的咨询公司。眼下他虽然留在中国,但却表示,在他的100位客户中,很多人要么拥有外国护照,要么就希望拥有外国护照。大部分人都拥有或管理着中小型企业,这样的企业受到了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的挤压。
“有时候,你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状况也会变得非常复杂,”彭磊说。“有些人可能会希望生活在更透明、更民主的社会里。”
Amy Qin、Adam Century和Patrick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Wary of Future, Professionals Leave China in Record NumbersBy IAN JOHNSON November 02, 2012
BEIJING — At 30, Chen Kuo had what many Chinese dream of: her own apartment and a well-paying job at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But in mid-October, Ms. Chen boarded a midnight flight for Australia to begin a new life with no sure prospects.
Lik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who leave each year, she was driven by an overriding sense that she could do better outside China. Despite China’s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es in recent years, she was lured by Australia’s healthier environment, robust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freedom to start a family in a country that guarantees religious freedoms.
“It’s very stressful in China — sometimes I was working 128 hours a week for my auditing company,” Ms. Chen said in her Beijing apartment a few hours before leaving. “And it will be easier raising my children as Christians abroad. It is more free in Australia.”
A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prepares a momentous leadership change in early November, it is losing skilled professionals like Ms. Chen in record numbers. In 2010, the last year for which complete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508,000 Chinese left for the 34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make up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at is a 45 percent increase over 2000.
Individual countries report the trend continuing. In 2011, the United States received 87,000 permanent residents from China, up from 70,000 the year before. Chinese immigrants are driving real estate booms in places as varied as Midtown Manhattan, where some enterprising agents are learning Mandarin, to the Mediterranean island of Cyprus, which offers a route to a European Union passport.
Few emigrants from China cite politics, but it underlies many of their concerns. They talk about a development-at-all-costs strategy that has ruined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 deteriorating social and moral fabric that makes China feel like a chillier place than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Over all, there is a sense that despite all the gains in recent decades, China’s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jectory is still highly uncertain.
“People who are middle class in China don’t feel secure for their future and especially for their children’s future,” said Cao Co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who has studied Chinese migration. “They don’t think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stable.”
Most migrants seem to see a foreign passport as insurance against the worst-case scenario rather than as a complete abandonment of China.
A manager based in Shanghai at an engineering company, who asked not to be named, said he invested earlier this year in a New York City real estate project in hopes of eventually securing a green card. A sharp-tongued blogger on current events as well, he said he has been visited by local public security officials, hastening his desire for a United States passport.
“A green card is a feeling of safety,” the manager said. “The system here isn’t stable and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I want to see how things turn out her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Political turmoil has reinforced this feeling. Since early this year, the country has been shocked by revelations that Bo Xilai, 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most senior leaders, ran a fief that by official accounts engaged in murder, torture and corruption.
“There continues to be a lot of uncertainty and risk, even at the highest level — even at the Bo Xilai level,” said Liang Zai, a migration expert at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 “People wonder what’s going to happen two, three years down the road.”
The sense of uncertainty affects poorer Chinese, too.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ommerce, 800,000 Chinese were working abroad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versus 60,000 in 1990. Many are in small-scale businesses — taxi driving, fishing or farming — and worried that their class has missed out on China’s 30-year boom. Even thoug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been lifted from pover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ich-poor gap in China is among the world’s widest and the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dominated by large corporations, many of them state-run.
“It’s driven by a fear of losing out in China,” said Biao Xiang, a demographer at Oxford University. “Going abroad has become a kind of gambling that may bring you some opportunities.”
Zhang Ling, the owner of a restaurant in the coastal city of Wenzhou, is one such worrier. His extended family of farmers and tradesmen pooled its money to send his son to high school in Vancouver, Canada. The family hopes he will get into a Canadian university and one day gain permanent residency, perhaps allowing them all to move overseas. “It’s like a chair with different legs,” Mr. Zhang said. “We want one leg in Canada just in case a leg breaks here.”
Emigration today is different from in past decades. In the 1980s, students began going abroad, many of them staying when Western countries offered them residency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uprising. In the 1990s, poor Chinese migrants captur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y paying “snakeheads” to take them to the West, sometimes on cargo ships like the Golden Venture that ran aground off New York City in 1993.
Now, years of prosperity mean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the means to emigrate legally, either through investment programs or by sending an offspring abroad to study in hopes of securing a long-term foothold.
Wang Ruijin, a secretary at a Beijing media company, said she and her husband were pushing their 23-year-old daughter to apply for graduate school in New Zealand, hoping she can stay and open the door for the family. They do not think she will get a scholarship, Ms. Wang said, so the family is borrowing money as a kind of long-term investment.
“We don’t feel that China is suitable for people like us,” Ms. Wang said. “To get ahead here you have to be corrupt or have connections; we prefer a stable life.”
Perhaps signal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the topic has been extensively debated in the official media. Fang Zhulan, a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wrote in the semiofficial magazine People’s Forum that many people were “voting with their feet,” calling the exodus “a negative comment by entrepreneurs upon the prote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ir rights in the current system.”
The movement is not all one way. With economies stagnant in the West and job opportunities limite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returning to China was up 40 percent in 2011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established high-profile programs to lure back Chinese scientists and academics by temporarily offering various perks and privileges. Professor Cao from Nottingham, however, says these programs have achieved less than advertised.
“Returnees can see that they will become ordinary Chinese after five years and be in the same bad situation as their colleagues” already in China, he said. “That means that few are attracted to stay for the long run.”
Many experts on migration say the numbers are in line with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xperienced huge outflows of peopl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1960s and ’70s, even as their economies were taking off. Wealth and better education created more opportunities to go abroad and many did — then, as now in China, in part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political oppression.
While those countries eventually prospered and embraced open societies, the question for many Chinese is whether the faction-ridden incoming leadership team of Xi Jinping, chosen behind closed doors, can take China to the next stag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
“I’m excited to be here but I’m puzzl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path,” said Bruce Peng, who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last year at Harvard and now runs a consulting company, Ivy Magna, in Beijing. Mr. Peng is staying in China for now, but he says many of his 100 clients have a foreign passport or would like one. Most own or manage small- and medium-size businesses, which have been squeezed by the policies favoring state enterprises.
“Sometimes your own property and company situation can be very complicated,” Mr. Peng said. “Some people might want to live in a more transparent and democratic society.”
Amy Qin, Adam Century and Patrick Zuo contributed research.
|
||
|
Posted: 01 Nov 2012 11:07 PM PDT
|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
|
Posted: 01 Nov 2012 10:49 PM PDT
|
|
Posted: 01 Nov 2012 09:44 PM PDT
中国问题学者,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其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首发活动。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仍存在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德国之声中文网)10月29日,历史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应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在港参加了其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活动。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在港首发(音频)
1974年至1997年间,麦克法夸尔相继发表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 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大跃进,1958-1960年》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来临1961-1966 年》三部"文革前史"英文版。北京求实出版社曾在1989至1990年间出版该书的中译本, "八九民运"后中共当局收紧言论空间,此书第三卷中译本一直难于问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此次首次出版第卷中译本并增补原中译本删减部分,10月末《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全版中译本在香港正式发行。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认为麦克法夸尔的文革史是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少有的杰出著作。该作品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来解释文革的政治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
麦克法夸尔中文名字为马若德,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包括《中苏之争》、《毛统治下的中国》、《中国政治:六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近期与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为其最重要的作品。另外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革史迄今二十余年,这门课程也成为哈佛的经典课程之一。
"毛能发动文革,应政治体制上找原因"
旅美学者胡平对德国之声表示,麦克法夸尔的书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文革这段历史,胡平作为文革时代的亲历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后来不得不接受刘少奇这一派的务实政策,这样他在党内上层的威信降低,他就担心大权旁落,也担心死后象斯大林一样受到批判。后来在林彪的帮助下,他从强调经济建设改成阶级斗争。"
《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关于文革的定性为"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动乱",对此他持保留意见。
杨继绳说: "是毛泽东错误发动,但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为什么全民疯狂的跟随,为什么能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造成那么多人的死亡和牺牲?我觉得得从政治制度上寻找原因,是从1949到1966年整个制度体系造成的,这个制度体系再加上对毛泽东的高度神化和崇拜才导致文革的发生。"
 文革中投入狂热运动中的群众 文革中投入狂热运动中的群众
"中国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太多了"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与麦克法夸尔会面后,在《金融时报》上撰文也指麦克法夸尔对文革的研究,为现实解读"薄熙来事件"、"重庆发展模式"等提供了贴切的背景和深层脉络:"薄、王那一帮领导干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舆论制约、更不受道德制约的黑帮式权力,为别人造就了一片红色恐怖, 同时也为自己埋设了一串烈性炸药。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则是不一定的。
对此重庆民间思想家、历史学者王康认为时至今日,毛泽东及其主张在中国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拥趸:"他把他自己的思想和数以亿计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这是毛泽东至今都在中国社会底层或有一部分阶层里有深厚土壤的奥秘,不破除这个奥秘中国很难进步,对文革的认识也无从谈起。在中国社会不管党内,还是民间,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太多了。"
胡平认为复杂的文革历史不可能完整复制,但不同的人包括执政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选取文革片段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或批判或肯定。对未来中国执政领导人会不会有此倾向,王康表示有待观察,而这也需要读者从不同的关于文革、毛泽东的历史著述中作出他们的判断:要民主、法治还是毛泽东?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
|
Posted: 01 Nov 2012 10:02 PM PDT
蓝哈达,金哈达
——荔蕻大姐的五七华诞纪实
朱 毅
十点钟——该是将军的女儿在温榆河激情抗辩的时刻,我正凝立在锡林格勒草原深处,久久凝视着一缕缕蓝色的火焰:那是一条条系紧在元上都中心遗址荆丛上的蓝色哈达,在蓝天白云下、在草原的劲风中狂舞着........
那一瞬,心中幻化着元上都遗址入口处成吉思汗巨型壁雕群,又似乎感觉王处、孙队、正蓝旗的巴彦局长、达赖司机.......不约而同注视的目光。可他们想象得到吗?——
正是那一瞬,升腾草原民族大历史深处骄傲的那一缕缕蓝色火焰,在我的心中,幻化成了一条金色的哈达,金色的巾帼——当代华夏飘拂在茉莉与荆丛中的价值与守望、坎坷与英勇、从容与骄傲!
其实对于我,这只是昨夜蒙古包盛宴的继续罢了:是的,既然辛亥百年的秋瑾祭日,我为冯先生的《林昭<秋风辞>全注释》序,那《大悲至善:秋瑾.林昭.当代囚徒王荔蕻》的正标题,正是我不可遏止的怀念与敬意;那么当两位蒙女,一位捧着雪白的哈达,一位端着酥油茶,在国宝簇拥中第一个为我唱响祝福的蒙歌的时候,谁又能遏止我把雪白的哈达,遥遥献给正在受难的大姐呢?!
此刻,我的身边,今天五七华诞的王荔蕻,在两度朝阳看守所与两个诺奖之间飘拂着价值中国故事与高度的王荔蕻,就披载着金色的“哈达”,被祝寿的诗人们温馨簇拥着。
照例,年纪居长的我领衔举杯:
“今天,荔蕻大姐57华诞,为起伏沉浮之间这温馨一刻,我们举杯祝福!!”
次第祝寿的诗人们是:阿尔,龙龙、李楠、海豚天天,精心准备了祝寿诗——《秋之黑方》的龙龙,强本夫妇及女儿——感谢这位年青的母亲:正是她当年宣读苏州诗人黑沨为铁玫瑰园圣女双雕揭幕诗!
同祭林昭而相识,又邂逅在后冬至同一黄丝带时刻。八聚铁玫瑰园——从林昭雕塑第一次审像,到圣女双铜像揭幕日最后送别张志新的亲人们,荔蕻大姐是我一直的、乃至每一个细节的依傍。她与老虎庙们对底层维权芸芸众生乃至雕塑家夫妇的关注与保护,尤其他灵魂导演的福州“4.16”,更为我远远望尘莫及,是网络华夏同鉴共仰的。可那是一头乌青乌青头发的大姐啊。不料炼狱归来,揭开艾晓明教授送的绒线帽,大姐竟满头花发!——同在北京,两年多以来我们仅此一见。实在思痛!好在网络晨昏,慰见大姐不仅价值姿态依旧昂扬,且在两个特岗、四度转世中更其悲悯,更其执着,更其骁勇守望着精神中国的每一个细节!只是最近网传她被撞过一次,以致今日寿宴,虽屡屡善酒的大姐始终以茶代酒,滴酒不沾,既无大碍,深觉庆幸!
我岂能不代为陈平福呼吁联署团队的其他所有人——王书瑶、艾晓明、甘粹、葛洵,为荔蕻华诞深深祝福?!
却是龙龙的祝诞,让寿宴价值激情澎湃到最高潮——
“大姐,医院这么近。你的紅方碎了
黑方还在超市
法国酒——过去裝着马賽曲的旋律
旋律开始时穷人开始幻想
正如骄傲开始时人类非常可怜
还我叙事曲,还我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和他的咳嗽
你们在延安大学邂逅、恋爱
借助一把鋤头和小提琴,让大地环环紧扣
大姐,你的青春还在赶牲灵
大姐,你还要为自己活三次
一次在日內瓦
一次在福州
一次在朝阳区看守所
...........”
想不到同赴温岭为林希翎迎骨的评修,也是今天祝寿嘉宾之一——林希翎的墓志铭,也凝聚着她与小路的辛劳与奉献。评修奔过来拥抱以示重逢的惊喜。那一瞬,却触动我连绵而惨然的感慨:京杭特快上,小路一次次面对评修与我,惊忧痛惜于灵魂飘香的失踪;殊不知,那也正是朝阳看守所的阴影再度逼近荔蕻大姐之时!——律师阅卷表明:有司就是那个日子,开始侦缉荔蕻福州案的。更料不到的是:温岭——林希翎墓志铭,苏州——林昭自由碑,竟成花年我必被维稳的重责之重,以致有司不辞万里,专车光顾……
也是在席间,终于再见海豚天天——艾晓明教授实拍温榆河庭外的陪同者。她特别感慨与流徙中的我那次长长的通话。是的,我也至今犹记她的絮叨,她的鄙夷,她的愤慨,尤其当她叙及温榆河法庭外摄录着的艾晓明遭遇刻意纠缠的时候......
身边就是金帼白发,就是艾晓明纪录片让《田喜回家》、让《阳光洒在地上》的王荔蕻大姐。四下福州,两度牢狱,王荔蕻一身担当了后六四最浩大的人权抗争、最严酷的“冬至”。最是大姐乃至大姐精心安排的庆生宴,诠释着行动、担当者的高贵,联系着平凡与中国高度。一次次在这种场合邂逅的,多非公知,也非大腕,却都是为行动而担当、而流徙着的十二月党人——中国的十二月党人!
正是在十二月党人苦难这样的意义上,九月九日,对于我最是精心,而又刻骨铭心:九月九日,独夫寂灭,华夏新生,志士永恒——张志勤与甘粹一致接受在这个日子为圣女双雕揭幕;九月九日,荔蕻大姐在铁玫瑰园为我张罗着圣女双(铜)雕揭幕的每一个细节;九月九日,艾晓明教授、刘晓原律师、刘沙沙们又出现在温榆河,艾教授在法庭外一次次向身边的国安赠送《阳光洒在地上》光盘;九月九日,三国安兄弟陪我从长城外放逐地直驰广州:在餐车的西藏啤酒中我品位着十二月党人流徙的滋味,也构思着次日的教师节上该对学生们诉说什么;就是精心选择这样的九月九日,温榆河法庭匆匆宣判:被告王荔蕻以滋事罪处判九个月!
今天绝非滋事:大姐是由警车送达寿宴酒楼的。 “他们不断地‘走吧,走吧’”,大姐揣度着:也许过几天就要胡佳“被安徽”那样“被海南”了;不甘流徙,也不愿警车袭扰中国“十二月党人”的温馨,所以,今天我只能也必须从传达室便装特警眼皮下开溜——据说:归来时分连同出租车费,都被一一记录在案;今天,福州三网友们,连同五湖四海的十二月党人,只能在微博中遥祝大姐;福州同步上网了去年终审日提早为大姐庆生的十人照——去年的今日我正在李九莲喋血处取土,只是在此刻的照片上我才看到:游精佑、吴华英们统一身着特制的服饰,多么庄重的感恩!多么十二月党人的湘濡以沫、患难情深!然而,十八大大限的今天,除了小小的诗人群与终席后仍然从长安街赶来的一位诗人,即使近在北京的十二月党人们——老鬼、崔卫平、郭于华们,也只能在网上祝福大姐与遥想金哈达风采了.......
禁锢,遮没,限制……其实,巾帼,就是这样被西伯利亚的风雪镀金的啊!
谁能说,这不正是中国深度的金色?
也许正因如此,突然想起王静梅——杨佳妈妈今天缺席,荔蕻大姐才遗憾得惊呼起来!几乎每一个杨佳祭日都与大姐相对相依的王静梅!把自己、天国儿子连同狱中大姐三份1522元送到草场地,就沉默着转身离去的王静梅!邂逅杨佳妈妈,也正是在大姐、老虎庙主持吴华英庆生会上,我深深理解而且同样为此深深遗憾着。只见大姐立即打开手机走向窗边。对话之后是欣慰:原来骨质增生住院着的王静梅,正想发祝诞短讯呢,可手机没电,恰好从医院赶回家充电来着……
啊,飘拂的金哈达!中国十二月党人湘濡以沫的温馨!
10月28—29于北京
|
|
Posted: 01 Nov 2012 09:50 PM PDT
臨近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競爭激烈即將投票之際,一場世紀颶風襲擊美東,造成巨大災難,但是美國人面對災情和選情,一派鎮靜,因為他們知情。大洋彼岸,中國共產黨的一場空前激烈的權力爭奪,也臨近揭曉,社會表面一切如常,百姓冷漠,卻因為他們對國家大事不知情,更無參與感。由薄熙來事件發端,已延續九個月的這場權力鬥爭,是海外和西方媒體幾乎每天不斷的熱門話題,現在終於要搬到中共十八大的舞台上來。無數鏡頭將要聚焦在這個最後的共產大國,未來將由一班什麼人來統治?他們的權力結構和統治方式將會發生什麼變化?
中共執政已經六十二年,他們像一個原始部落一樣實行家族式的宗法管治。大家長包辦一切,先是毛澤東獨霸二十七年,接著是鄧小平說了算,約二十年,死前還和幾個元老安排了兩代接班人,江澤民核心、胡錦濤為首又撐了二十年,來到沒有強人的今朝。這是薄熙來野心勃起的背景。說來好笑,他們拒絕西方的普選制,也拒絕孫中山奉行的選賢與能,甚至不講政績操守,搞出一條年齡畫線的遊戲規則。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七上八下」就是老江的獨創。九七年他七十一,超齡不退,定年限七十二。混到十六大,要拉李瑞環下,就改年限為六十八,小木匠活生生下台。中組部李源潮零六年制定領導幹部任期規定,並未讓七上八下法定化,但實際上嚴守如儀。現在「七常委」之爭,俞正聲、汪洋都受制於這個潛規則。說前者老了,後者少了。即使習近平的上位,也得益於太子黨曾慶紅這位「造王者」的心計:十七大他退下,讓出空位給習,否則十八大的王位就落在胡錦濤的團派手上。
年齡畫線後面掩護的是派系勾結、利益關聯和老人干政。這是中共接班制的實質。現政治局委員夠「七上」的有十人,其中至少五人和江澤民有恩惠關係,包括二張和敢於跟四億網民為敵的劉雲山。傳習近平和江胡兩「婆婆」三代敲定最高權力七人常委名單,便不足為奇。外界無不以劉雲山的入常與否,作為觀察未來政改的風向標。如果網絡嚴控不得絲毫鬆動,還能指望其他什麼?如果有意以劉雲山而排斥汪洋,毋寧說是十八大最大的敗筆。也折射出習近平政治上的無奈與脆弱。
明報報導,習有鑒於政治局常委人事的激烈分歧,主張在十人中差額選出七人。若果如此,那是邁出實質性改革的第一步。不過,可能是旁觀者的一廂情願吧。君不見十三大開創「差額選舉」以來,就像趙紫陽提倡「重大事情要讓人們知道」早已被人遺忘一樣,任何列入憲法黨章中的漂亮承諾,實踐中都變成了謊言。我們對十八大不敢輕易樂觀,那是有太多的記憶使然。可以保留的是,一份追蹤撲朔迷離的新聞事件的職責。十八大之後,我們再來分析中國的新局面。
(原載開放雜誌2012年11月號,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Posted: 02 Nov 2012 09:44 PM PDT 杰安迪 报道 2012年11月03日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周一,海南省举行“喜迎十八大”文艺演出。
北京——中国共产党官员们将于下周降临首都北京,参加指定下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仪式。在这里我给想庆祝这场盛会的人提个建议:把气球留在家里。
这座有2000万人口的规模庞大的城市正在下大力量应接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各种有潜在漂浮能力的东西,如气球、信鸽、乒乓球和遥控的玩具飞机,都上了可疑物的名单,也许它们可能携带抗议信息,搅乱这场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
而且这只是政府规定和限制的一个极小部分,这些规定和限制在互联网上流传,但从未得到官方证实。在为期一周的党代会期间,这些规定和限制看来可能会使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具挑战性,一位省公安厅的官员把党代会的准备工作比作“一级战备”。
最近,菜刀已经从商店的货架上拿下,互联网的访问速度莫名其妙地慢、好像粘稠糖浆的流速,像CNN和BBC这样的国际新闻频道已经从高档健身俱乐部的电视机中消失了。
在“老书虫”这家颇受欢迎的英文书店,原来的中国政治和历史书籍销售区现在摆满了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惊险小说、育儿指南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Victoria Beckham)的时尚宝典《额外的半英寸》(That Extra Half an Inch)。
一位店员无奈地耸耸肩说,“我们只是重新布置一下,党代会之后它们就会回来。”
最近,这份开列党代会期间市民所面临的不便和妨碍的清单,已经变得比会后发布的公报还要长。马拉松比赛、学术会议、宠物收养集市,电影制作和爵士音乐会都被取消或推迟了。不仅是在北京,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商业交易都已经冻结了数周,企业雇员说。一位沮丧的互联网设计师说,在党的元老们于会议结束时公开推出新任最高领导层之前,没有新网站可以上线。
音乐人高晓松在中国版的Twitter上发了一条帖子,说凡带有“死”或“下”字样的歌曲都已经被电视台临时取缔了。高晓松写道,“刚刚眼看着一歌手翻唱《死了都要爱》被毙,提醒下同行。”
中国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警告股市交易商把市场波动维持在最小水平,不要在政治大事之前“违逆北京”。
有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主要是男性的党代表们,可能对官员们为减少让与会者从无休止的演讲和闭门饭局中分心的事情而采取的极端行动尤为失望。据为性工作者提供社区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人士李丹说,至少一半的首都妓女都被逮捕,或被驱赶出城。
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而言,党代会无异是给他们的一记耳光。在全国,如果没有数千名、至少也有数百名活动人士和政府批评者被软禁在家,或被迫远离首都去“度假”,而且常常是在警方看守的陪同下。
藏籍博主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说,国安部人员逼迫她本月离开自己的北京寓所。她在老家西藏首府拉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猜,他们觉得我们这样的人不和谐。他们就是想在他们的重大会议期间,让我们这些人从视野中消失。”
北京的著名律师浦志强说,共产党的无端恐惧只会增强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他说,“如果政府真实地代表普通老百姓,他们不需要这么草木皆兵。共产党只顾自己,他们认为必须总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操纵人民的意志,才能维持稳定”。
到目前为止,北京出租车受到的限制引起了最多的不满。司机们接到命令被要求解除后座车窗的开窗功能,以免乘客从人民大会堂上风口散发反政府信息。人民大会堂是本次党代会的会场,这一毛泽东时代的雄伟而精雕细做的建筑物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
政府向出租车司机许诺奖励,如果他们告发“企图散发携带横幅的气球、或带有信息的乒乓球”的乘客。作为“零传播”规定的一部分,司机们被提醒对后座进行检查,以确认乘客是否可能留下不适宜的政治信息。
司机李伟旭(音译)抱怨说,“这实在太麻烦了。”他说,他最关心的是,政府是否会为他报销更换手摇车窗把手的费用,他被要求把把手拿掉。
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党代会准备工作,占据了这个幅员辽阔国家里忧心忡忡的政府官僚们的全部精力。根据《人民日报》的消息,掌管国家安全的中国领导人周永康在7月的一次高官参加的会议上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是开好十八大的重要前提,是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首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
在中国西北部青海省一个偏远的、藏族为主的县,当地官员发誓要严惩被发现销售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照片的市场小贩、或任何“散步淫秽、色情及庸俗信息”的居民,同仁县(Rebkong)政府下发的一份通告宣称。在中国另一端的沿海省份山东,2.6万名官员被派入乡村和小城镇,以确保农村“基层”在党代会之前平静无事,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
就连最难制服的中国政府批判者、艺术家艾未未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套上了缰绳。艾未未说,警方看守建议说,他可以对几乎任何事情公开讨论或写评论,只要不涉及即将召开的十八大。
他说,“说实在的,这还可以吧,因为党代会只是那些人的一次内部会议”。他用略带嘲讽地语气强调“那些人”,“那和我没关系,说真的,和其他任何人都没关系。”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Amy Qi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Restrictions Pave Path to a Transition in ChinaBy ANDREW JACOBS November 03, 2012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Hainan Province on Monday celebrated China’s coming 18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with choreography and flags.
BEIJING — A word of advice to anyone hoping to celebrate the gathering of Communist Party apparatchiks who are about to descend on the capital next week to anoint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 Leave the balloons at home.
As this sprawling city of 20 million people steels itself for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ll sorts of potentially buoyant objects — balloons, homing pigeons, Ping-Pong balls and remote-control toy airplanes — are finding their way onto lists of suspicious item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carry protest messages and mar the meticulously choreographed political spectacle.
按图放大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The window crank of a Beijing cab was removed to prevent riders from tossing out antigovernment messages.
And this is just a tiny por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ules and restrictions, circulated on the Internet but never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that seem likely to make daily life especially challenging during the weeklong congress, which one provincial police department likened to a “state of war.”
In recent days, kitchen knives have been removed from store shelves, Internet access has mysteriously slowed to the speed of mo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news channels like CNN and the BBC have disappeared from television sets in upscale health clubs.
At the Bookworm, a popular English-language bookstore, the section previously devoted to Chinese politics and history has been stuffed with Stephen King thrillers, child-rearing guides and Victoria Beckham’s “That Extra Half an Inch.”
“We’re just reorganizing,” one employee said with a helpless shrug. “They’ll be back after the party congress.”
In recent days, the list of interruptions and inconveniences has grown longer than a post-congress communiqué. Running marathons, academic conferences, pet adoption fairs, film productions and jazz concerts have all been canceled or postponed. Not just in Beijing but across the country, business deals at state-run enterprises have been frozen for weeks, employees say, while one frustrated Web designer said no new sites could go up until after party elders publicly presented the new slate of top leaders at the end of the congress.
The musician Gao Xiaosong, posting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witter, said songs with the words “die” or “down” had been temporarily banned from television. “I just witnessed a singer who sang ‘Die for Love’ have his performance killed,” Mr. Gao wrote. “Colleagues should take this as a lesson.”
All facets of Chinese society have been affected.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warned stock traders to keep market volatility to a minimum and not “buck Beijing” ahead of the political event.
And some of the predominantly male delegates arriving from around China may be particularly disappointed by just how far officials have gone to eliminate distractions from the endless speeches and dinners taking place behind closed doors. At least half the capital’s prostitutes have already been arrested or driven out of town, according to Li Dan, whose nonprofit group provides outreach to sex workers.
For Chinese dissidents, the congress has already proved itself to be a slap in the face.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activists and government critic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been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or forced to take “vacations” far from the capital, often in the company of police minders, according to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sering Woeser, a Tibetan blogger, said national security agents forced her to vacate her Beijing apartment this month. “I guess they consider people like us inharmonious,” Ms. Woeser said, speaking by phone from Lhasa, the Tibetan capital, where she grew up. “They just want us invisible during their big important meeting.”
Pu Zhiqiang, a prominent lawyer in Beijing, said the party’s paranoia served only to fuel public disillusionment. “If the government actually represented the common people, they wouldn’t need to be so strict,” Mr. Pu said. “The party is so cynical they think the people must always be distracted and manipulated in order to maintain stability.”
So far the restrictions on Beijing taxis have produced the most complaints. Drivers have been ordered to disable their rear-window controls lest passengers toss antigovernment messages upwind from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imposing Mao-era confection on Tiananmen Square that is the site of the congress.
Cabdrivers have been promised rewards for turning in passengers “who intend to spread messages by carrying balloons that bear slogans or Ping-Pong balls bearing messages.” As part of the “zero spread” rules, drivers have been reminded to check rear seats for unseemly political messages that might have been left by passengers.
“It’s terribly inconvenient,” complained one driver, Li Weixu, who said he was most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ould reimburse him for the cost of replacing the hand-crank window handles that he was required to yank off.
Preparations for the party congress, many months in the making, have preoccupied anxious government bureaucrats across this vast nation. “Safeguard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s a very important precondition for the opening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nd is the priority task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level of government,” Zhou Yongkang, the nation’s security chief, said during a meeting with top officials in July, according to People’s Daily.
In one remote, largely Tibetan county in Qinghai Province, in China’s northwest, officials vowed harsh punishment for market vendors caught selling photographs of the Dalai Lama, the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or for anyone “spreading obscene, pornographic and vulgar messages,” according to a notice circulated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 Rebkong, or Tongren in Chines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country, in coastal Shandong Province, 26,000 officials were sent to villages and small towns to make sure the rural “grass roots” remained pacific ahead of the party congress,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news agency Xinhua.
Even the country’s most irrepressible government critic, the artist Ai Weiwei, has been largely reined in. Mr. Ai said his police minders suggested he could publicly talk or write about almost anything — except the coming party congress.
“To be honest, it’s O.K. because it’s just an internal meeting for those people,” he said, emphasizing “those” with faint derisio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Or with anyone else, really.”
Amy Qin contributed research.
|
||
|
Posted: 02 Nov 2012 09:35 PM PDT
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 2012年11月03日
北京——中国的政治由共产党及其各个强大家族和派系所把持,所以当一名前党总书记的儿子说出,这国家几乎算是个“法西斯”国家时,确实值得一听。
已故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因为改革意识太强,于1987年被迫辞去总书记一职。他的儿子胡德平于2005年底,在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一群中国商人和环保人士说出了上述观点。(因为他父亲的倒台,胡德平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成为了一名所谓的“没落太子党”,但他的血统依旧让他成为一名红色贵族。)
七年后的今天,政治改革压力不断增加,下周四开始的十八大将在同一座人民大会堂内宣布新一届领导人,而胡德平的话语却依旧萦绕不散。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它又将去往何方呢?
根据我的笔记,以下就是胡德平当年所说的话:“不管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专制,哪怕是法西斯,这个国家的人民仍然需要正义。他们寻求的东西,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正义。”
今天的中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吗?
这可以举出几个特点来说明,先拿一党制来说吧。从毛泽东死后开始的经济改革,已经使这个国家通过其国有企业的盈利而变得极为富有。中国从一个贫穷的专制国家,变为一个富有的专制国家。而它的国企也跻身世界上最富有企业的行列。
尽管有了一点放松,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依然受到严重妨碍。一些高级官员公然蔑视民主。法院则服从党的领导。
官方的口号变本加厉地鼓吹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这个概念植根于民族主义的神秘情结,流行在上个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之间。
“这些迹象早就存在了,”知名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我觉得有一个清晰的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趋势,而这种法西斯主义源自那些掌权者们仍在增长的权力。”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他说,在这里权力只为权力服务。
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带来权力的分享,而只不过是脱掉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外衣,且并未出现令人信服的价值体系来填补这个空缺,他说。
“掌权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王力雄说。
“今天的这个利益集团没有意识形态,”他说,“他们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他们只能依赖强权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拿不出使人民信服的目标。所以这个国家依赖强权去压迫社会并实现其目的。我想,这些强权拥有者们大概别无选择了。”
的确,我们面对着一些大问题。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更加个人化的例子,本周一有五个人来到我们在北京的公寓,检查了我们的护照、签证和居留许可证,其中几个说他们是警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十八大前加强安保措施的一部分。这令我想起了胡德平说过的话。
在他们离开了几秒钟之后,屋子外的走廊里发出了喧嚣的吵闹声。透过观测孔,我看到一名中国邻居正在大声斥责警察多管闲事。这类突击检查令人恐惧并且遭人憎恶,但是人们却越来越敢于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当然,除了“法西斯主义”,也有其他的术语被用来形容这里的情况。许纪霖是一位知名的知识分子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写道,“国家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篇去年的短文中,许纪霖警告说,在共产党和政府声称只有自己可以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氛围下,中国可能会“重新踏上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走过的那条死路”。
而韩国延世大学的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教授认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例如纳粹德国实行的制度,与今天中国发生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之处。
“如何定义法西斯主义绝对是关键,”他在来自首尔的电话中说。
“对于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最有力的反驳之一,是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元素是大规模动员”,其中包括相关的符号象征和集体动作编排,例如希特勒的纽伦堡集会,德勒里说。毛泽东做过这类事情,但当前的领导层并未这样做,他说,因而表明这个术语并不完全合适。
“我仍然认为当前的领导层,就算不是反毛泽东主义,那也是非常的后毛泽东主义。”德勒里说。
然而对于王力雄来说,即便没有毛泽东的领导魅力,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威胁。他指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已经越来越多的针对其他国家。
当他听到这个曾经是禁忌的词汇,这个丢给共产主义之敌的绰号,被中国精英阶层的一员,甚至是一名关键成员,来描绘中国的政治方向时,他感到吃惊吗?
“我听到这个词并不吃惊,因为那些在领导层中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并不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说。
翻译:林蒙克
——纽约时报中文网
LETTER FROM CHINACan China Be Described as 'Fascist'?By DIDI KIRSTEN TATLOW November 03, 2012
BEIJING — Chinese politics is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powerful families and factions, so when the son of a former party chief says the state is virtually “fascist,” it’s worth listening.
That’s what Hu Deping, son of the late Hu Yaobang, the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forced to resign in 1987 for being too reform-minded, said to a group of mostly Chinese businesspeople and environmentalists in late 2005,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Tiananmen Square. (Because of his father’s fall, Mr. Hu is outside the mainstream of power, dubbed a “nonprinceling,” but his pedigree still makes him a party aristocrat.)
Seven years later, with pressure for political reform mounting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to be announced in that sam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which starts next Thursday, Mr. Hu’s words continue to reverberate. What is China today, and where is it headed?
Here’s what Mr. Hu said, according to my notes: “No matter how authoritarian this society is, even fascist,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still want justice. One thing they seek is profit, and the other is justice.”
Is today’s China fascist?
To cite a few characteristics, starting with the one-party state: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that followed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t has grown immensely wealthy through its state-owned companies, some of which rank among the world’s richest. What was once a poor, authoritarian state has become a rich, authoritarian state.
The rights to speak and associate freely remain tightly hobbled despite some relaxation, and some top officials openly scorn democracy. The courts obey the party’s directives.
Official slogans increasingly exhort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a concept rooted in a mystical sense of nationhood popular with fascist thinkers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signs have long been there,” said Wang Lixiong, a prominent writer and scholar. “I feel there is a very clear trend toward fascism, and the source of fascism comes from the ever-growing power of the power holders.” China is “a police state,” he said, where power rules for power’s sake.
The passing of Mao did not lead to power-sharing, it just stripped China of its Communist ideology, and no convincing value system has filled the gap, he said.
“Power has become an interest group,” Mr. Wang said.
“Today the interest groups have no ideology,” he said. “Their goal is to protect their own profit and power. They can only rely on power to rule, because they have no goal that convinces the people. So the state relies on power to suppress society and attain its objectives. I think there’s no other route the power holders can go.”
These are large issues. On a more human scale, I was reminded of Mr. Hu’s words on Monday when five men, several of whom said they were police officers, came to our Beijing apartment to check our passports, visas and residence permits, almost certainly part of the stepped-up security before the Party Congress.
Seconds after they left, a loud argument erupted in the corridor outside. Through the spy hole I watched a Chinese neighbor loudly berate the police for meddling. The checks are intimidating and resented — and people increasingly are not afraid to say so.
For sure, terms other than “fascism” are also used to describe what’s going on. Xu Jilin, a leading intellectual and history professor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Shanghai, for example, writes that “statism” has grown dominant in the past decade.
In an essay last year, Mr. Xu warned that in an atmosphere wher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e claim the sole right to represent the “universal interest,” China may “re-tread the broken road of 20th-century Germany and Japan.”
For John Delury, a professor at Yonsei University, in South Korea, there a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ic fascism, such as Nazi Germany’s, and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Absolutely the critical thing is how to define fascism,” he said by telephone from Seoul.
“One of the strongest objections to using the word fascism is that a central element of fascism was mass mobilization,” which included the symbolism and choreography associated with, for example, Hitler’s rallies at Nuremberg, Mr. Delury said. While Mao did that, the current leadership does not, he said, a sign that the term does not exactly fit.
“I think still this leadership is very post-Mao, if not anti-Mao,” said Mr. Delury.
Yet for Mr. Wang, fascism is a threat, even without Mao’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He points to rising nationalism at home, increasingly directed overseas.
Does it surprise him to hear what was once a taboo word, an epithet to be hurled at the enemies of Communism, used by a member of China’s elite — even if a critical member — to describe China’s political direction?
“I’m not surprised to hear it, because they know, the people in these ruling circles, they don’t think it’s strange, they know what’s happening,” he said.
|
||
|
Posted: 02 Nov 2012 12:51 PM PDT
|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
|
Posted: 02 Nov 2012 11:36 AM PDT
十七届七中全会开幕,难产的十八大终于要走进日程,干扰美国大选的是台风,阻碍十八大召开的是权斗,各派政治势力个个都是满身伤痕,十八大虽有看点,但是达成的不过是脆弱的政治平衡。
深秋十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城应该还是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景致,但是却出现了满城皆见"红袖章"的红海洋。王府井、西单一个个商业大厦里,"红袖章"比顾客还多,售货员人人都戴着"平安志愿者"的红箍。京郊的长线公交车进京,乘客沿途要两次下车盘查身份证,有红袖章的优先放行。
140万是维稳时代最后的规模
30日,北京市举行了"十八大安保动员誓师大会",号称动员出 "志愿者"达140万。不算正式保卫的军警队伍,仅这个数字就是十年前包括武警、公安、便衣、保安在内的十六大安保大军的2.3倍。 十年前,我曾经描述过十六大的"安保壮举":"出门遛狗,除了看见三五成群的'小脚侦缉队',又戴上几十年久违的红袖章,满街溜达之外,竟然意外地看到一个骑着破自行车,挎着旧编织袋,拿着铁钩子的捡破烂的,胳膊上也戴着'人民治安员'。惊讶之余,不免对他留意一下,只见他无暇顾及社区的环境和行人,一门心思盯着的只是楼后的垃圾道,在每个垃圾道前,都要跳下车,用铁钩子扒拉一番,淘过之后,飞身上车,又直奔前边的垃圾道去了。"这段话,曾经让丁子霖老师笑出了眼泪。  十八大前北京戒备森严 十八大前北京戒备森严胡温维稳十年,北京对文革发明的红袖章早已见怪不怪,年年两会、十七大、08奥运、60年大庆,北京的保安大军一次都比一次壮大,但是大到140万,遍布"交通、旅游、文化、商业、建设、环卫等系统党员公务员和治安志愿者",还是让人倒抽一口冷气,需要这么多人保卫的一个会议,是不是就该不开了,直接宣布人事结果不是更省事! 扑朔迷离之中闪出差额选举的亮光 一位老朋友,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过的老学者,通常隔三差五总来个电话,讲讲新消息。就在"北戴河会议"之后,海外传媒争相报道十八大人事版本的数个月里,却接不到他的电话了。本周主动给他打了电话,只听他说:"谁上谁下,关我们什么事呀!我从来不去打听,别人说,我也不想听。"这反映了为数不少的老党员对十八大越来越漠不关心的态度,更不用说年轻人了。 就在政治局9月28日召开会议,宣布十八大推迟到11月8日召开之前,还有"十七届七中全会要在十一长假抢时召开"的消息传出来。据悉,十一长假中央确实一直在开会,为定人事盘子在做紧张的准备,轮流召集中委、中纪委委员和省部级新贵来京进行摸底投票。摸底结果,中央满意。这使得十八大有可能进行扩大差额选举。这个说法成为有关十八大扑朔迷离的信息中,跳闪出来的唯一的一道亮光。 据悉,十八大的差额选举,不但在中委进行,还要扩大到政治局和常委。常委是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之外,只对其他人进行差额选举。中委、政治局、常委,差额比例不同,大概是10%-30%。以常委为例,如果是7人制,习李除外,确定6名候选人,差额比例也达到20%,如果是9人制,8名候选人,差额将接近15%,9名候选人,差额接近30%。 确定习近平、李克强不参加差额选举,属于中国特色,是中共高层经过反复协商,保证十八大平稳交接的一个决定。如果形势有变化,一旦控制不住,常委很可能不实行差额选举。 海外媒体有关常委的预测,出现多种版本,与多次、反复摸底投票的结果有关,也与高层激烈的人事争议有关。  习近平不需差额 七中全会的头一天,将确定中委和后补中委的候选名单,2号将确定政治局名单,确定常委是7人还是9人。也同时确认是否进行差额选举,如果确认,还要确认候选名单。
胡锦涛能否再连任两年军委主席?
10月17日李锐、杜导正、何方几个党内老民主派,原定要和一位更高层的人物研究给中央上书,而且已经写好,内容是劝胡锦涛十八大"裸退"。早晨,这位高层人物来电话:"中央已经定了。"上书行动只好作罢。据悉十八大胡锦涛连任军委主席,"江规胡随",是两天之前,15日左右中央做出的决定。 10月23日国内财新网率先报道了中央调整了总参谋部、成都军区和空军部分高级将领,据悉得到了官方默许。25日国防部网同时刊出解放军四大总部的人事调整,正职同时易人。26日新华社报道9常委分别到北京展览馆参观 "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长长的国家领导人名单之后,特别点出两位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许其亮的名字。常、许二人刚从装备部部长和空军司令员位置上卸职,年龄均在限,属于实力派将领。新华社的报道预示十八大他们两人军中职务还会得到高升。至此,十八大新军委名单已经大部分列出,所剩只是11月15日十八大一中全会军委主席的候选人名单到底是谁?是习近平?还是胡锦涛?也是七中全会确认的重要问题。将是十八大火爆看点。
胡锦涛两年里也是一波三折
2011年,是中共政治力量集结较量的重要年份,胡温十年的政绩遭到严重非议,赞成"重庆模式"的太子党台上派刘源、张木生重新提出"新民主主义",以"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对胡温做了贬斥。甚至用"官二代"与自己的"红二代"进行分野,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十八大"太子党"要掌权, 要"重整山河"的决心。
以胡德平代表的"宪政"改革派,虽然在体制内人力单薄,但是借十一届六中全会和"粉碎四人帮"几个纪念日,举行了大规模座谈会,邀请参与结束文革的红色家族共同呼吁重新启动改革,坚决反对腐败,重棒还是打在胡锦涛身上。 胡锦涛不仅面对太子党,还有"太上皇"江泽民仍旧强大的政治势力,可谓前边有狼群,后边有猛虎。胡与各方协商所要求的条件,首先是十八大"分得一杯羹"――连任军委主席两年。 在王立军逃馆发生之前,胡锦涛连任要求连连遭到拒绝,有山穷水尽之态势。温家宝3.14讲话,促使"重庆事件"彻底爆炸,十八大太子党接班的铁三角,最强势,最令人畏惧的一角坍塌,最害怕清算的江泽民最先提出对薄熙来"按照刑事处理"。这实际上提升了胡锦涛的力量,胡掌握着平衡的权力,要保薄熙来的政治力量,转而向胡去求情。  "江规胡随" 胡留任军委主席? "江规胡随" 胡留任军委主席?4月10号双规薄熙来,将薄谷开来移交司法,当时中央拿出推迟十八大,常委扩大到11人的方案,这对胡锦涛最有利。就像十六大一中全会,是按照常委7人和9人两个方案进行选举。一中全会结束,记者会等了半个小时才召开,就连新华社也不知道即将走出的新人都有谁。最后走出的是9个人,是江泽民拍的板,他的人马占据压倒多数。十年之后还要影响到十八大。 4月,胡锦涛首先确定政治局女委员刘延东入常,刘即属太子党,又与胡锦涛在团中央共事多年,而其父与江泽民养父是革命战友,刘是栖息三界的人。胡推刘入常,是为推自己的嫡系人马入常铺路。江泽民在西山,开始频繁会见常委和元老,让彭博社公布他与星巴克老总见面的消息和照片,以加大内外影响。11人的常委方案很快便推翻。十八大真正的权斗开始。 未完待续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德国之声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Posted: 04 Nov 2012 05:57 PM PST 原文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國作家莫言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政府一反先前態度,熱烈唱和,內地網民與知識界則有連番熱議,文學造詣與政治表態之間,是否亦不存在很大的空間?今期本版摘譯本身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曾翻譯《零八憲章》的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擬發表於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評論文章,且看他如何談論莫言的文學作品。
莫言自90年代遇上的一大難題,是尋找他能長遠採用的寫作嗓音。《紅高粱家族》雖然確是突破,但只因為在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中,中國作家憑着「闖禁」就能出名了,而《紅高粱家族》一口氣闖了兩個禁區:性事解放、就中日戰爭說真話。到90年代,未打破的禁區比前少了,還留下來的(如六四屠殺、高官貪腐、台灣、西藏、新疆)卻都是生人勿近的非常禁忌。
被欺壓歸咎低級官員
他最後找到了一把拉伯雷風的聲音,而且比拉伯雷更貼近世俗。人類擁有許多動物天性——吃喝拉撒、打鬥嚎喊、男女媾合,有時也有一些動物未必有的特質,例如欺侮、合謀、背叛。莫言的表達中充滿嘲諷,也包含了許些狂想,以至有論者將之比作馬奎斯的「魔幻寫實主義」(但實際上他有沒有讀過拉伯雷或馬奎斯,卻令人置疑;當中有所雷同,卻不能認定他受到二人的影響)。
莫言寫社會底層的人,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就明顯站在飽受地方官欺凌的貧農一邊。在當下的中國,同情被欺壓者是有相當市場的,但必須注意,莫言寫被欺者命運的手法,跟劉曉波、鄭義等異見作家不同。劉和鄭譴責整個中國專制制度,包括最上層的人,但莫言等建制內的作家斥責的是地方上的污吏惡紳,高官在圖畫中不會出現。把人民苦難的責任推在低級官員身上,是中國統治精英素來的做法。在網絡崛起的今天,信這一套的人已少了很多,但這論調仍行之有效。莫言這類作家很清楚這一點,他們未必喜歡,但卻接受了讓步,這就是留在體制內的代價。
莫言寫了好些涵蓋中國20世紀歷史相當部分的全景角度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開始的中國虛構小說潮流,但對於體制內作家,如何處理大躍進或文革等歷史片段,是一大難關。莫言的方法是,在處理「敏感」事情時,就讓某種瘋狂鬧劇登場。《豐乳肥臀》在第六章寫到大躍進時,莫言拿毛澤東的荒唐農業政策(例如提出動物雜交以繁殖全新物種)大開玩笑,卻隻字不提其後的大災難。兔羊雜交有何不可?書中一名豐乳女志工道,就是把領導的精子打進豬子宮也沒問題!當場爆笑滿堂。
笑談敏感議題
對中共而言,這種寫作模式是很管用的,不僅因為它避開了嚴肅地直面歷史,也因為這種文章能起安全閥的作用。這些敏感話題至今仍然具潛在爆炸力,領導人將之當笑話看待,也許比起完全禁談更屬上策。
莫言想過的,是否比他最終付印的多?對這問題我們最起碼應持開放的態度。他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劉曉波時,說希望劉曉波能盡早獲釋,有關發言迅速被內地媒體網站刪掉,外界估計可能是惹怒了當局,視之為良心言論。
他這言論當然有其價值,但我認為比起良知和勇氣外,有一個更合理的解釋。無論是體制中人或異見人士,中國公安和文宣官員都會跟名人們保持緊密接觸,提示他們的公開言行。作為諾貝爾獎級別的名人,可以想像,莫言被約談應該不止一次,他們也一定有談及如何回應關於劉曉波的問題。這是全世界記者都會問的問題,他總得有個「說法」。從當權者角度,什麼說法能把傷害減到最低?如果莫言說劉曉波是罪犯、坐牢有理,他的形象勢將受損,他獲獎的榮耀也會受損,而他的榮耀是中共希望鞏固和利用的。可是,要他真心挺劉曉波也不行。最佳做法就是這種溫和的中庸論調,說希望他早獲自由。
曲線論劉曉波
莫言其中一句話令這說法尤其可信。他重複希望劉曉波獲釋時說:「……盡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我不認為他知道劉曉波現在的健康情况。這句話會否是為當局日後容許劉曉波保外就醫鋪路?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擬)
文 林培瑞
編輯 黃海燕
——何晓青推荐
|
||
|
Posted: 04 Nov 2012 05:53 PM PST
为什么是莫言?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一公布,诺贝尔奖真的成了炸药奖,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炸开了锅,舆论哗然,熟悉和不熟悉莫言的人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是莫言?”
先不论民众的冷嘲热讽,称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是向中共十八大“献礼“,以“纠正”前几次(包括挪威的和平奖)颁给异议分子的错误,单说莫言面对他抄写毛著及党员身份等质疑时,心虚又得意地宣称自己得奖“是文学的胜利”,言下之意,用文学标准评价他的作品是够格的。莫言还抱怨许多批评他的人“根本没读过他的书”,那么我们就来读莫言,看看他的作品质量到底如何?
十几年前,冲着莫言的大名,买了一本《丰乳肥臀》,但读了几十页就读不下去了。几年前,听到他又写了一本“广受好评”的《檀香刑》,忍不住好奇拿来看,却是边看边恶心,勉强看完,留下的全部印象就是吃了一碗变质的杂碎,还是混有蟑螂、苍蝇的。如今,莫言得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奖,我不得不反省,是不是我鉴赏力不够?于是,再耐心读他的得奖作品《蛙》和《生死疲劳》,勉强看了半部还是看不下去。无独有偶,王蒙和查建英做客凤凰电视台“锵锵三人行”节目谈莫言得奖,查建英说莫言的长篇都看不下去。
当然,超一流的好作品也不一定让大多数人接受,尤其对非文学专业的人。比如:篇幅过长的托尔斯泰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240万字的《追忆似水年华》;过于深奥艰涩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过于幽玄迷离的卡夫卡的《城堡》等等。
那么莫言的作品也是这样的阳春白雪吗?
尽管看不下去,为了做出自己的判断,硬着头皮把《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蛙》看完。
东施效颦的“模仿现实主义”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的颁奖词说:“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魔幻现实主义,顾名思义,就是魔幻加现实主义。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首的一批南美作家开创的文学流派,其代表作是惊动西班牙语文坛的《百年孤独》。作品讲述西班牙移民后代布恩蒂亚百年前在南美“沼泽雾锁”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叫马孔多的村庄,是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离的未开化地,愚昧落后的马孔多人对一切荒诞不经都深信不疑。所以,小说把现实与神话、传说、梦幻杂糅,情节奇谲多变,打通客观与主观、人间与鬼域的界限,反应了拉丁美洲的一段蒙昧历史。
莫言模仿“魔幻现实主义”讲“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以《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为代表作。《生死疲劳》用中国佛教的六道轮回的观念,让土改中被处死的地主再生为驴、牛、猪、狗、猴讲述遭际,差强人意地模仿了“魔幻”形式。而《丰乳肥臀》在人物和角色关系的构思上套用(说得不客气是抄袭)《百年孤独》。比如《百年孤独》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母亲乌尔苏拉,照顾几代子孙,《丰乳肥臀》里也有一个母亲上官鲁儿,也是照看几代子孙;《百年孤独》里有一对双胞胎、有一个活了二百岁的神人,有姑侄乱伦,有蕾梅黛坐着毯子飞上了天;《丰乳肥臀》也有一对双胞胎,有一个活了一百二十岁的仙人,有姑父和侄女乱伦;有一个鸟儿韩飞上了树,《百年孤独》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内战,《丰乳肥臀》书写成中国的抗战和国共内战,雷同的还不止这些。简而言之,《丰乳肥臀》不过是用中国历史事件的元素在《百年孤独》的框架里填充。
然而,莫言在极尽模仿之能事时,忘了《百年孤独》从表现手法到人物心理和精神状态,与故事的背景地印第安古老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十分贴切。读《百年孤独》时,你觉得书中人物怪异和荒诞,但放在吉普赛人、各种巫术、半原始的穷乡僻壤的氛围中,似真非真又不失真。
而“高密东北乡”地处中华儒家传统文化土壤深厚的齐鲁平原,百年来,虽然封闭落后于城市,但并非是与中国社会进程脱节的蛮夷之地。莫言把《百年孤独》中的凶杀、暴力、血腥、乱伦硬贴到《丰乳肥臀》上,把偷情等人欲横流的现象放大成乡村的主流,是现实中找不到对应图景的胡编乱造。比如,上官鲁儿的九个子女,是跟姑父(还得到姑母认可)、牧师、和尚、土匪等七个人苟合和野合出来,已经匪夷所思,和洋牧师生出的野种金童还是金发碧眼高鼻梁,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村,真有这样的母子,即使家人不管,也早被乡邻的唾沫淹死了。
如果说,莫言小说的“魔幻”部分东施效颦,那么“现实主义”部分能否给读者几个让人难忘的人物呢?比如,我们在托尔斯泰的《复活》里为深具宗教忏悔意识的聂赫留道夫感动;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认识他同时代的“多余人”;我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震撼;从鲁迅的《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沈从文的《边城》里看到翠翠清纯如泉的美好人性;同情又不无嫌恶地看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病态的乖戾阴鸷等等。
可惜,你在莫言的作品里读不到类似的人物。莫言几部长篇写了上百个人物,却没有一个是丰满独特让读者动容的。按文学评论家李建军的说法,莫言小说中的人“都是扁平的”。比如,《丰乳肥臀》中写了八个姐妹,但你无法区分她们的个性,或者说她们之间可以互相交换,是莫言分配她们去嫁给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土匪、当妓女,而没有人物本身性格发展的脉络,一些次要人物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结果,看莫言自己得意的几部作品,就像看一台春晚,他就是春晚的导演,指挥演员拖拖拉拉皮皮沓沓热热闹闹表演四个小时,但帷幕一合观众什么也没得到。当然,就像春晚总有一、两个好看的节目,他的长篇也有一些出彩的段子和不少活泼的语言,但在他随意随性毫无节制的笔触折腾下,那些别出机杼颇具魅力的语言和情节,经过恣肆汪洋滔滔不绝啰嗦赘言的混合,成了暴雨后的泥石流,泥沙俱下冲决一切,再美的风景也都毁坏殆尽了。
玩赏残忍和“卡通化”
所以,莫言借用“魔幻现实主义”,与其说是发挥自己侃大山式的“发散性”思维,不如说是掩藏自己缺乏大作家细腻刻画人物的功力,披上“魔幻现实主义”这件织锦外袍,也不过是化腐朽为神奇,以遮盖美化袍子底下的肮脏败絮。
“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反传统文学的审美观念,表现一种审丑的美学,同时,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作者又遵循“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创作原则,也就是审丑也有它内在的合理性,也要有一个度。比如,《百年孤独》里的雷贝卡在苦恼时吃泥土、墙灰、蚯蚓、水蛭;蕾梅黛丝“用自己的一撅儿粪便在墙上画小动物。”都是病态的癖性,世界上也存在这样的异人。
然而,莫言知道,要成为“大作家”就不能限于模仿,还要有超越“创新”精神。于是,他极尽变态夸张之能事,把不能自圆其说的故事,道听途说的无头案,掺上凶杀、暴力、血腥、乱伦,用审丑的“美学”敷衍成章。他在《檀香刑》里展示凌迟钱雄飞的虐行:一刀一刀要割足五百刀,最后一刀下去方可毙命,早一刀晚一刀都算刽子手的失败,而且每一刀割哪个部位、大小、薄厚都有严格的标准,洋洋洒洒写了十八页的篇幅,看到这里,读者也在跟着受刑。莫言把残暴的酷刑当艺术品来设计,犹如绣花姑娘勾勒了一款新图案,再用丝线一针一线精心刺绣。读者在反胃时不由悲叹,从容写下这些文字的作者,要有多么坚韧超常的玩赏丑恶的心理。
同时,再好的艺术形式也不适合任何题材,莫言用“魔幻”表现“土改”、“三年自然灾害”、“文革” 等浸透苦难的政治运动,过于荒诞的卡通化人物和情节,消解了战争的悲壮历史的沉重,不堪回首的悲剧演成突梯滑稽的喜剧。
《生死疲劳》中写到,许多老干部忆起文革总是血泪斑斑,把文革期间的中国描绘成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恐怖的人间地狱,但我们这位县长却幽默讲述自己的遭遇:“他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还有一段说:“车上的红卫兵在‘大叫驴’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打倒奸驴犯陈光第!’‘大叫驴’的嗓门,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大雁肉味清香,营养丰富,集上的人疯了,拥拥挤挤,尖声嘶叫着(抢大雁),比一群饿疯了的狗还可怕。”抢大雁变成了混战,变成了武斗,最后十七人被踩死,伤者不计其数。
批斗治好了的顽症,批斗演变成争抢大雁,且死伤人数胜过武斗,黑色幽默也兜不住如此无厘头。
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魔幻”和“意识流”还给了莫言一个便利,就是“小说可以这样胡言乱语(莫言看了《喧哗和骚动》后的体会)”。无拘无束地胡编乱造,使莫言愈写愈顺,愈写愈得意,用四十多天完成《生死疲劳》,用九十多天完成《丰乳肥臀》,可以比肩二十五天完成长篇小说《赌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还债几乎不打草稿的巴尔扎克。但莫言也是这样的天才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最关键的长知识的十年赶上文革,基础文化都是小学程度,文革后再补也补不上童子功。有自知之明的人,一个严肃对待写作的人,会格外用心,以勤补拙,就像傅雷提醒张爱玲那样,“要多写,少发表”。
但莫言觉得自己的腹稿快于自己的笔,一个个构思像阿拉伯的石油,在沙漠上打个洞就咕噜咕噜往外冒。连给他启蒙的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只看了半部,心态浮躁如此,哪里会静心学点文史哲儒道释。然而,作家可以胡编天方夜谭,却无法乱造学识,所以,莫言小说里的硬伤比比皆是,而且犯得都是常识性错误。
莫言捏造了一个历史上不曾有、也根本无法实施的“檀香刑”——“一根檀香木橛子,从犯人的谷道钉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维持5天不死。”他大概以为人体从食道到肛门有根直通的管道,却不知从谷道(肛门)插进去的木棒抵达喉咙前早就穿破心肺大血管了,受刑者当场毙命,哪里还让莫言折磨几天几夜?说一个人能受“檀香刑”,等于说一个人能够(几天之内)“刀枪不入”。莫言只要翻一下解剖书,或者请教一下学医的,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
《丰乳肥臀》里的母亲是和牧师(神父?)玛洛亚有奸情的教徒,他俩的私生子金童(我)也受了洗。既然是牧师(神父?),那么他们应该是新教教徒(中国俗称基督徒),然而,写到后面,母亲一会儿喊:“天主啊,睁眼看看!”一会儿又一口一句“上帝”。莫言不知,天主教徒只称“天主”不会说“上帝”,基督徒相反。玛洛亚因教堂被鸟枪队占领就跳楼自杀,基督教教义严禁教徒自裁,一个牧师(神父?)怎么会轻率犯禁?可见莫言不懂教义信口开河,也不知神父和牧师的区别。到最后金童对母亲说:“娘,您死了,成佛了,成仙了,到天堂里享福了,再也不用受儿子拖累了。”莫言以为教徒像他糟蹋文字一样,随便亵渎信仰,竟然佛教、道教、基督教一锅煮了。
《蛙》里姑姑对人说已去世父亲:“正是家父。”对故世的父亲称“先父”这样的常识莫言都乱用。书中还有“顽抗政府”“万端无奈”等费解的句子。诸如此类的低级错误,如果吃不准查查字典,本来不难纠正,可见莫言毫无敬业之心。难怪他只学到大作家的皮毛和形式,没有把握他们的内涵和精髓,最后画虎不成反类犬,他的作品既没有传承中国传统文学的长处,又没学好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成了不古不今不中不洋的四不像怪胎。
莫言得奖后有人开始称他为“大师”了,看看犯这么多低级错误的“大师”,中国人的人文素养降到了何等地步,但也不作为怪,垃圾时代出垃圾大师,只是让中国上世纪前半学识渊博的真正大师情何以堪!
莫言作品中的人性表现在哪里?
上述种种显示,也许说莫言的长篇小说是胆大妄为的“故事会”,莫言是有奇思异想的故事篓子还过得去。然而,莫言不安于这样的名分,尤其在得奖后,他要拔高自己作品的层次。他认为,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评委,是因为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性,因为自己一直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超越了地区和种族。”
可惜,我们在莫言的作品中没看到应有的人性。
《丰乳肥臀》里的玛洛亚牧师(神父?)和母亲野合后生下了我(金童),母亲抱着我去受洗,受洗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但牧师(神父?)却和咬着母亲奶头的我抢(摸)母亲的乳房,嘴里还不停地骂我“小杂种”。这里,父亲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私生子,而且是牧师(神父?),本该交织出羞愧惊喜慈爱等复杂感情,正是莫言挖掘人性的场合,莫言竟然写得如此粗卑下流,何况牧师(神父?)再淫乱,也不至于在孩子受洗时如此玷污上帝(天主?)啊?
对比《巴黎圣母院》里爱上艾斯米拉达的主教的内心煎熬;《牛虻》里主教蒙泰里尼对自己的私生子亚瑟欲爱不能、欲弃不忍的深沉痛苦,莫言的笔下的牧师(神父?)对私生子的态度的人性在哪里?
《蛙》讲的是用残酷手段执行计划生育的故事,但书中受害者没有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对抗,迫害者也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反省。小说主角妇产科医生姑姑,坚定执行党的政策,“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毫无人性地亲手流掉“两千多个”孩子,也没见她在做党的工具和不忍心之间的矛盾心理和人性挣扎。老年的姑姑还是被蛙神索命才幡然醒悟,而且停留在“因果报应”的层次,“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姑姑把“受折磨”’与“赎罪”混为一谈,没从觉醒的人性提升到战胜盲从党性实为兽性的高度,使赎罪显得浅薄和苍白。
“左”“右”逢源内外通吃
莫言得奖后,热捧他的人替他辩解说,眼睛不要盯着他中共官员身份,要看他在作品中如何书写,含蓄地提醒人们,他的作品是“反体制的”。
是的,不能定性莫言的作品是“歌德派”,相反,《丰乳肥臀》里的地主、国民党都有不少正面表现,甚至入侵中国的日本兵的随军军医还救了孕妇(母亲)和双胞胎婴儿的命,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很负面。以至书出版后,那些参加过抗日的老作家大骂莫言颠倒黑白,抹黑共产党。《蛙》对计划生育的残忍也多有揭露。自相矛盾的是,莫言对丧失人性的计划生育的评价却是相反的,他为中共辩护:“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如此大煞风景的话,一笔抹杀了计划生育中的所有罪恶,更别说把类似陈光诚那样对抗计划生育的人物写进书里了。
《生死疲劳》里写蓝脸坚持单干不入合作社,受尽压力和磨难,到八十年代推行包产到户,宣告了他的“胜利”,批判和否定了中共三十年的农村政策,似乎是“反体制”的。但《生死疲劳》和《丰乳肥臀》的故事都跨越六四,但书中决口不提六四,如果公开谈六四无法出版,他可以用拿手的“魔幻”手法来隐喻一番,可惜,他不敢!所以许多读者说,莫言的长篇小说最多能看前半部。原因是,政府允许论说的内容,他写得比较放开,政府绝对禁忌的话题,他决不涉及,只能草草了结,精明盘算分寸拿捏都十分到位。
有人对此抱以同情,认为在无形的政治高压下,丧失自由心灵的莫言奴役成性,潜意识里习惯成自然地左右逢源,弄得左支右绌两面不讨好。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还不尽然。莫言在回答关于《生死疲劳》的采访中说:“时间和被遗忘的关系,或者是历史跟遗忘的关系——时间、历史、遗忘。西门闹(小说中被冤杀的地主)当初作为一个满腔怨恨的灵魂,甚至是不屈的灵魂,在阴差阳错之下转成各种动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的仇恨都会慢慢的消减,所有的痛苦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淡化掉,或者被渐渐遗忘掉。……我想进入21世纪以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逐渐在倡导一种和解,或者说在提倡一种和谐,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
这个调门简直就是为中共的“和谐社会”代言,在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诸般罪恶——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还没清算的情况下,提倡遗忘除了帮闲还能说明什么?在共产国家生活过的大作家,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凯尔泰斯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一个主题,就是“人和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因为有了记忆才能不忘刻骨铭心的痛,才能反思造成痛的制度之恶,人性之恶,才能寻求正义,才能最终抚平创伤,得到真正的和谐。
其实,以“左”和“右”的观念检讨莫言,或者用他作品中的“反体制”色彩与他言行的“相悖”证明他人格分裂,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莫言是一个有啃煤渣和常年饿肚子经历人,他原初的写作动机是“做作家能够三顿吃饺子”,可悲的是,衣食无忧后他仍没摆脱这种小农意识,养尊处优后功名利欲变本加利。中国的惨烈历史,民族的灾难,农民的疾苦,社会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堕落等等,都不过是他书写时拿来利用的道具,就像他把“魔幻”拿来做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莫言超越了“左、右”,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左、右观念,一切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准星。他可以右手写“批判体制”的作品,左手拿体制给予的所有好处,还有纯文学商业化,一样都不少。如此理念主导下写出的长篇小说除了大杂烩,哪里会出深具人文主义情怀的艺术品?
厚颜无耻的犬儒告白
莫言在2009年的一个专访中,回答是否看过赫塔·穆勒(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时说:“看过(穆勒作品)片段介绍,没什么出奇之处,这种东西很多。很多东欧跑到西方的作家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像米兰·昆德拉这些。几乎所有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流亡到西方的作家,都在用这种笔法来写作,控诉他们母国在政治高压下这种荒诞的现象,控诉人的自由在这种社会中受到的压制,以及人的精神扭曲,基本都是这个路数。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在控诉黑暗的政体这个高度上,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伟大的文学一定是超越政治的,肯定不是把控诉一个政体对人的压迫作为最大的目标。”
看到这里,不由哑然。
确实,纯粹从文学的角度而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索尔仁尼琴和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也许称不上伟大,但这个话由莫言说出来,可比大陆流行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没吃不饱饭的人说,西方社会的人都在减肥了,你的意识超前了。
一个对身边每日发生的罪恶视而不见的犬儒,竟大言不惭地蔑视用文学揭露共产社会真相的作家,一个身为作协副主席,任由政府监禁无数写作者而不敢发声,无论艺术水准还是道义理念根本无法攀比东欧反体制作家的附庸文人,却奢谈不屑局限于批判独裁专制,而要超越这个层次写伟大的小说,正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两字。
莫言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超越的见解,要像巴金晚年的反思,达到“他人有罪,我也有罪”的深度,“你如果不是一个受压迫者,你肯定是一个压迫者,在这样的社会里,你不是一个铁锤就是一个铁砧。”在他看来,控诉政治对人的压迫的作家只批判“他人有罪”,而没有上升“我也有罪”的高度,写出的作品不可能伟大。这话说得很好,但他真有这样的境界,何止要反思过去的“我也有罪”,现时现地他是作协副主席,是制造文字狱的“压迫者”,是帮闲帮凶的“现行罪人”,他要摆脱自己的罪性,首先就该丢弃作协副主席的宝座,他舍得吗?
不管莫言怎么贬低东欧反体制作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用文字记录的共产暴政,是反人类的共产历史的佐证,将和失败并最终消亡的共产史一起为后人阅读,而莫言的作品可以借诺贝尔的光环风靡一时,但早晚会成为中共文化的附属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莫言为什么能得奖?
有人会不解,有人会诘问,莫言如果像你说得这么不堪,他怎么会得诺贝尔奖?
这看似不可思议,却一点也不奇怪。
首先,莫言用南美的“魔幻”黏贴在高密上,还自鸣得意地自诩建立了“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但在大多数大陆读者看来,他的“王国”不过是穿着邋遢长衫马褂的中国人系领带戴西洋礼帽,不伦不类丢人现眼。他以糟蹋农村和农民形象为能事,煮出一锅浓浓的冠名为“魔幻”“高密东北乡”的怪味汤,大多数国人闻之如腐烂霉变恶臭的泔水,只有没经历过大陆当代历史,不解大陆民瘼的港台人吃来有点麻辣刺激,而西洋人更在莫言的恶癖中找到了臆想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觉得他的小说新颖奇诡,酸臭的怪味汤成了独特的东方珍馐琼浆。
所以,在对莫言作品的评价上,出现了奇怪的反差,港台读者高于大陆,外国——主要是汉学家——又高于港台,莫言成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美国的汉学家葛浩文就此迷上了莫言,他用去粗取精的译法,把一堆丑陋腌臜的石头清洗打磨,弄出译本比原作更有文采的奇观。所以,文章开头提到的查建英,莫言的中文小说看不下去,却说英文译本读得很有味。这样的“佳话”打破了翻译界的常规。人们所知的现象是,愈是精品愈难翻译,《红楼梦》翻成英文,能够传达六、七成意思已经很好了,反之,莎士比亚的作品翻成中文也可能同样如此。
至于莫言如何谄媚大江健三郎,甚至《蛙》用僵硬的给日本友人(大江健三郎的原形,比如喜欢萨特等情节)的书信形式编撰小说等说辞有诛心之嫌,这里略去不表。
总之,莫言成功了!
莫言得奖的后果
虽然我对莫言的作品提出了这么多异议,但对他得诺贝尔奖并不介意。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选错作家的例子并不少见,其中颁给中国作家和有关中国的作品——1938年美国作家赛金花因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大地》获奖——尤其离谱。如同外国政治家总是误判中国的政情,外国文学家也绝难评介中国文学,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在他们的谬奖榜上再多一个莫言不足为奇。何况,瑞典文学院可以给不够格的作家戴上桂冠,但揠苗拔高不能维持他们作品的生命力。如今,中国人还在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有多少人在读《大地》?
我介意的是给莫言颁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家肖亮说得好:瑞典文学院“给中国两个明确信号:一,在中国现存政治制度下,作家们已经可以公开出版具备世界级荣誉的文学作品,中国现有的言论出版制度不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二,中国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已经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认可,他们自许的三个代表之一——代表先进的文化己由西方国家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他们将再接再厉,继续维护和巩固这种便于自己捞取各种利益的制度。”
除此之外,就文学本身而言,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主流”作家,躲避崇高和理想精神,漠视现实社会的不公不义,远离民众对文学的期待,用各种文学流派和主义包装怪力乱神性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故事和人物,再设置各种文学奖项在小圈子里分赃,“主流”文学陷入自娱自乐的游戏境地。“主流”作家在抛弃大众时,他们的作品也被大众抛弃,失去了活水源头的文学处于濒死状态,莫言得奖是一支强心剂,将激励中国“主流”作家在文学歧路上越走越远,这正是大陆作协所乐见的绝佳效应。毫无疑问,被官方认可的文学愈“繁荣”,国内坚持自由写作的作家的空间就愈逼仄,这是瑞典文学院必须面对的颁奖给莫言的后果。
原载《自由写作》2012年11月号
——作者供稿
|
||
|
Posted: 04 Nov 2012 06:06 PM PST
核心提示:如果靠恐惧维持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新统治者们就得开始为共产党自身的前途恐惧了。随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正在以隐私的姿态静悄悄的进行着,共产党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留意到了这些信号,或者,像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继续试图维持一个行将走向灭亡的统治。
原文:China's Troubled Bourbons
作者:裴敏欣
译者:迈克 @Michae1S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加州,克莱门特: 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所阅读的书籍可以反映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近期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即将就任的常委们所读的一本书可能会让人们大为惊讶:他们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些即将在11月8号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接过权杖的中共领导人们,被爆出不光光自己阅读这本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条件的分析著作(指《可旧制度与大革命》——译者注),还把此书推荐给他们的朋友。如果这事属实的话,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何这些中共的未来统治者们要传阅一本关于社会革命的外国经典?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找到。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些中共领导人不管是直觉上,还是理智上,都已经感受到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生存,就像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一样。
秘密显露出来的忧虑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明显。资本撤出中国的数额现在创下了新高。调查显示中国的千万富翁们超过半数打算移民。在中国民主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中国候任领导人习近平会见了中国自由化的象征人物、政治改革者胡耀邦的儿子。虽然我们不应过度解读此次会晤,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下一任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江山已经不是那样稳固了。
关于未来几年内政治危机将会吞没中国的观点可能会打击到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对中共的力量和延续性都深信不疑的西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信心,使得这些人显得荒唐可笑。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对权力的执掌坚不可摧。但是很多逐渐显露的趋势,包括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或者只是在个别地被人们注意到的,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得共产党失去了公信力和控制力,而人民则获得了力量和信心。
一个趋势是涌现出了一批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商业精英、有声望的学者和记着、知名作家和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后,中共为了维持自身的安全,其中一个战术就是拉拢社会精英。但还是一些人,像胡舒立(她是两份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的创办者)、潘石屹(一个敢言的地产商)、于建嵘(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吴敬琏(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博客写作者像韩寒和李承鹏,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并且保持了自身的正直和独立性。
.
通过利用互联网和微博的优势,这些人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斗士。他们的道德勇气和社会才能,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支持(通过他们在微博上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者可以看出)。他们的声音经常在关于社会政策的辩论中有力地影响着政策的形成并把共产党置于被动。
对于共产党来说,这种发展态势明显是令人担忧的。中国政治的制高点,已经被迫让渡给了自发形成的社会力量代表,而共产党对此无力控制。中共对公众道德权威的垄断早已成为历史,而现今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是岌岌可危。
这种失势伴随了共产党的公信力在普通人中的崩溃。毫无疑问,共产党的不透明性、严格保密、和对谎言的强烈偏好显露了其在公信力上的问题。而且,在过去的10年间,一系列的丑闻和危机,包括公众安全、食品和药物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彻底地摧毁了共产党所残存的一点点公信力。
其中一个案例是2008年的毒奶粉案。官方对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的毒奶粉案在媒体上的封禁,不仅导致很多婴儿的死亡,而且使得普通中国人更加不信任中国当局。而在环境方面,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北京市民在关注每日空气质量报告时,比起自己的政府,他们对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布的同类数据要青睐得多。
对于一个已经完全丧失公信力的政权,维持其统治的成本是高得荒唐的——而最终它会再也无力承担这个成本——因为它必须不断的镇压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严重的暴乱。
由于科技革命发展的结果,集体行动的成本发生了戏剧性的下降,这使得镇压所带给共产党的好处越来越少。如果独裁者能够驱散人们,并且防止有组织的反对行动,他们就能维持统治。尽管现在共产党还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派,但它实际上每天都在跟有组织的抗议行动对抗。
根据中国社会学家们的估计,在中国,每天发生着500起暴动、集体抗议和罢工,这个数字比10年前几乎翻了4倍。随着手机和联网电脑的大规模普及,(抗议者)召集支持者和盟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得多。
此外,日渐增长的反抗也反映出:中国公众已经意识到,在面对愤怒的抗议者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显现怯意,并倾向于向公众让步。在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一些高调的集体抗议行动中:广东乌坎的土地纠纷,大连、什邡和启东的环保行动等,政府最终都做出了让步。
如果靠恐惧维持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新统治者们就得开始为共产党自身的前途恐惧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正在静悄悄的展开着,共产党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留意到了这些信号,或者,像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继续试图维持一个行将走向灭亡的统治。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者 于 11/04/2012 03:58: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