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或許因為接受韓國資訊,他們的國際認知和一般中國人不同。在崔家人心中,兩岸關係如同南北韓,和他們談及台灣時,他們都認可台灣有自己的政權,也認為它不屬於中國,總感嘆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台灣沒有自己的國際位置,對台灣很是同情。
文:阿潑(黃奕瀠)
那班從北京開往延吉(延邊朝鮮自治州的一個城市)的高速火車,中午發車,一天只有這一班。火車轟鳴前行,坐在裡頭,我只覺得窗外的世界越來越寒冷。「從這裡開始就是關外了。」夜幕拉下之際,列車停進了一個車站,許久未動,我往窗外好奇張望,卻辨識不出個所以然,坐我對面的大叔邊啃食雞腳,邊向我解釋說,這一站是山海關,也就是「天下第一關」,火車通過山海關,就進入遼寧省了。
這是一個為了防禦外族入侵而修築的關隘,也是萬里長城的起點,朱元璋奪天下後建了山海關,但明朝的覆滅也是因吳三桂在這裡引清兵入關。這是一條劃分胡蠻的邊界線,這條線仍隱隱存在於現在中國人的心中,彷彿是中國地理的天然坐標,如同這位大叔不加思索說出的那個詞:「關外。」
我剛好閱讀著前一天在北京書店購買的《尋路中國》,一開頭就是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開著吉普車,沿著長城駕駛的故事:「北方的草原是不設防的,而且在古代,這裡有許多遊牧民族,經常入侵他們不愛遷徙的鄰居。為了應對,中國人常常建城牆,這樣的防禦工事已知最早的歷史能追溯到西元前六五六年。」
古代中國的邊界並不明確,常因為戰爭或資源分配,讓邊界線產生進退,如今,這些邊防隘口不僅是地理分界,也攸關認同。我搭上火車前,先和幾個甘肅朋友在北京相聚,他們向我談起自己的故鄉時強調:「我們位在口內。」中國西北以星星峽為分界,甘肅是口內,過了星星峽的新疆,便被稱為口外——這類關防的概念,無非是種提醒,提醒自己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以及和「中國」間的距離。
在車站購買從北京到延吉的車票時,我好奇轉頭問詢問來自甘肅的朋友:「你知道這條鐵路的名字嗎?」他沒料到我會問這樣的問題,先是楞住,而後搖頭。我撇了撇嘴:「你們中國人都不必認識鐵路,為什麼我們得死背呢?」
為了聯考,我曾經耗費整個青春期背誦這些鐵路,它們以驕傲和屈辱構成軌道,架鋪在教科書中。它們像蟲子般在我腦子裡蠕動,填完試卷,便羽化成蝶,翩翩飛走,怎麼也記不得。我後來查資料,才記起這條直達圖們的長圖鐵路(長春到圖們)是日本「滿鮮鐵路直達」計畫中的重要一環,一九○五年起,日本積極打造一條朝鮮直達滿州長春的交通動脈,好連結兩個殖民地,圖們正是其隘口。鐵路往往是殖民者為了取得資源而鋪疊的軌跡,日本在朝鮮、台灣和遼東半島上築成一條一條的鐵路,「現代化」了這些舊中國的「化外之地」。
我搭乘的這班列車被命名為K215號,從北京到延吉,路程要耗費整整一天一夜。列車駛入吉林省後,日頭從天際線探出,此時方能細看窗外景致。北方冬色對我這種南國之人而言,顯得不可思議,我興奮得幾乎要趴上車窗好細磨雪國線條。不同於日本歐美,中國東北的農村別有特色,頂著直筒煙囪、貼著鮮紅春聯的屋舍在雪堆中浮列,春節的氣氛讓這陌生的景致得以漾著少許親切。
即使白雪覆蓋田園,卻仍看得出農地排列井然。「這套鐵路沿線的水田,都是朝鮮族世居之地。」臨行前我去拜訪一位朝鮮族教授,他對我解釋了這個族群的歷史。老教授個性直接豪爽,很有北方民族的氣魄,但他卻切切叮嚀,別將他的學校和名字說出來。類似這樣的叮嚀,都會提醒我正處在一個不同的世界——國家始終管控著某些領域,而像老教授這樣走過半世紀政治動盪的中國知識分子,儘管故事滿囊,卻更小心翼翼。
他是生活在中國歷史邊緣的那群人之一,生在延邊,但祖居朝鮮(北韓),如果用「關」來衡量,這裡比「關外」還更「關外」。因生活困苦,他的父親在一九三○年代來到東北——那時叫滿洲國——的一家輾米廠工作,從此再也沒有回去。像這樣由朝鮮到東北的經濟移民並不少,甚至遠在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發生饑荒時,便有不少朝鮮人來到毫無人煙的北大荒開墾;當然,更遠之前,高句麗王國的勢力也曾覆蓋在這片黑土地上。日本殖民朝鮮後,又有一批人為了尋找生活出路,渡過鴨綠江和圖們江逃到中國東北,其中也有少數人是因從事朝鮮獨立運動而逃難至此,如金日成。總而言之,這些後來在中國生根的朝鮮人,便是今日的「中國朝鮮族」。
「還有一批移民是日本占領東北後,強行帶來的朝鮮移民。殖民者發給他們一個村一個村的黑土地和水田,讓他們開墾。」老教授說,因為朝鮮是日本殖民地,所以日本人將最好的土地都分給朝鮮人,並將漢人趕到比較貧瘠的土地,他們只能種種高粱和大米。那時候的東北,日本人是最高級,朝鮮人次之,而後是滿人,漢人最低等,「所以從小我就覺得漢人怨恨我們,我們總被罵高麗棒子。」
移民,多半帶著些許不得已和苦衷,若是捲入權力或階級結構內,多半也會被貼上負面的標籤。面對不同於自己國籍、族群、文化、社會的「侵入者」,原本住民或許擔憂資源被掠奪、或者擔心血統受影響,或生存空間被剝奪,因此負面的貶抑始終存在,這正是高麗棒子一詞的社會根源。不論拉丁美洲、非洲後裔在歐美,或是東南亞配偶、移民在台灣,都有同樣的情況。
在台灣,移民強弱和先來後到並不太有直接關連。就和在東北的朝鮮人擁有最肥沃土地一般,漢人也將原住民驅趕到山林,奪取良田,只是,把握話語權的也是漢人,因而胼手胝足開墾荒地在台灣是美談而非掠奪。一九四九年後,權力者帶來了一批新的移民,權力者掌握了話語權,先到的移民反被壓制,心有不甘,埋藏在台灣社會之內的族群衝突,總像是一條不知何時燃燒的引線。理解他處移民的社會脈絡,亦能藉此省思台灣。
「營利事業及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113年5月首次申報,新制概念、放寬措施及關鍵字一次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12年度及112年1月1日起實施的「營利事業及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即將於113年5月首次申報。受控外國企業(CFC)是什麼?CFC制度實施前後的稅負效果為何?本文將帶大家一次看懂CFC制度!
營利事業及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分別自112年度及112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113年5月首次申報,其實CFC制度已在國外實施多年,其立意是防杜個人或營利事業透過境外低稅負區(如開曼群島)的受控外國企業規避我國所得稅負,藉此保障整體國民的權益。
受控外國公司(CFC)是什麼?
首先讓我們來說文解字,CFC是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的縮寫,中文是受控外國企業,Controlled代表受控,包括透過股權或實質控制,Foreign指低稅負的外國,最後一個
Company代表企業,包含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結合CFC這3個英文字,是指個人或營利事業對低稅負區的關係企業具有控制能力,這家低稅負區關係企業就是CFC。
CFC制度實施前後營利事業及個人的稅負效果為何?
●營利事業部分

Photo Credit:財政部賦稅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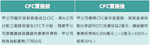
●個人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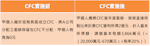
CFC定義、納稅主體、豁免規定:CFC制度三大關鍵字一次看懂
大家不用太緊張,並不是每個個人或每家營利事業都會適用CFC制度,以下從不同的股東身分,簡要說明哪些人、哪些營利事業會適用這個制度:

- 營利事業部分:適用於總機構在我國境內的營利事業,如果它在境外低稅負區(例如開曼群島)設立關係企業,且這家營利事業及它的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50%或對這家關係企業具有控制力,這家位於開曼群島的關係企業就是營利事業的CFC。營利事業應就這家CFC當年度盈餘,按直接持股比率及持有期間,認列投資收益,並計入同年度所得額課稅。

一張圖輕鬆掌握個人CFC制度。/Photo Credit:財政部賦稅署 - 個人部分:除符合剛剛提到的持股比率、境外低稅負區關係企業的條件外,還多加一個條件,個人、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當年度12月31日合計直接持有CFC的股份或資本額達10%,才需要按其直接持股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海外營利所得,與其他海外所得合計100萬元以上,才須計入個人同年度的基本所得額,且基本所得額扣除112年度扣除額670萬元後,按20%計算基本稅額,如果超過綜合所得稅繳稅金額,表示繳不夠,就須繳納差額稅款。
- 此外,我們在CFC制度還訂有豁免規定,如果CFC有實質營運活動或CFC當年度盈餘微小(微量門檻),就免依CFC制度計算CFC所得。
- 豁免1規定:CFC實質營運活動
CFC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且僱用員工在當地實際經營業務;同時,CFC當年度消極性收入(如投資收益、股利、利息、權利金等)占總收入比率低於10%。只要CFC符合上述所有條件,免依CFC制度計算所得課稅。 - 豁免2規定:CFC當年度盈餘在700萬元以下
個別CFC當年度盈餘在700萬元以下也可豁免,但為了避免營利事業或個人設立多家CFC分散當年度盈餘來適用這個豁免門檻,又訂了防弊規定,即營利事業或個人(個人部分包含與其合併申報綜合所得稅的配偶及受扶養親屬)直接持股且沒有實質營運活動的全部CFC當年度盈餘或虧損,即「正負相抵」合計在700萬元以下,免依CFC制度計算所得課稅。
- 豁免1規定:CFC實質營運活動


營利事業或個人居住者如果在低稅負區設立關係企業,且對它有控制權,無論CFC是否符合豁免規定,都要在今(113)年5月申報所得稅時依規定格式填報CFC相關書表及檢附證明文件,一方面可檢測自己有沒有CFC課稅問題,另一方面也可確保正確誠實申報,以維護自身權益喔!
CFC新制上路,首次申報放寬措施!
為讓制度運作順利,去年度12月底財政部也修正了部分CFC制度執行細節,包括調整微量豁免門檻之防止濫用規定、對非低稅負區轉投資事業決議分配111年度及以前年度盈餘數額提供免列CFC當年度盈餘加計項目之過渡措施、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FVPL)評價損益得選擇延後至實現時計算損益,提供首次申報的放寬措施如下:
第一項「微量豁免門檻之防止濫用規定」指上圖CFC豁免2規定中判斷全部CFC當年度盈餘合計是否逾700萬元之計算範圍,僅考慮納稅義務人直接持有股權且不具實質營運活動之CFC當年度盈餘合計數。
第二項CFC獲配源自非低稅負區採權益法認列轉投資事業於113年3月31日前決議分配111年度及以前年度盈餘數額,免列分配年度CFC當年度盈餘加計項目,惟於所得稅申報期限內(113年5月31日前),應提示足資證明該盈餘分配之文件。
第三項放寛納稅義務人得選擇CFC當年度盈餘排除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FVPL)評價損益,俟處分或重分類時以實現數計入CFC當年度盈餘,但一經選定,原則上不得變更。
CFC首次申報,你準備好了嗎?
今年是CFC制度實施後的首次所得稅申報,呼籲大家多多使用網路或手機報稅,不只省時、方便,還能減少民眾到國稅局的交通時間及等待時間。另外也提醒大家,務必在所得稅申報前先檢視個人或營利事業是否適用CFC制度,如果適用,就應於申報時依規定格式揭露CFC相關資訊及檢附文件;如果對於申報文件的準備有所疑問,也可以於財政部賦稅署網站反避稅專區(https://www.dot.gov.tw/htmlList/ch_389)查詢,或透過免付費諮詢電話0800-000-321了解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