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为一个自觉、积极、创造性的读者,去发现“文学的意思”
//

“文学阅读是比文学写作更难以扑灭的‘地火’,在岩层下奔突、运行。在我们阅读的时候,日常的无聊、琐屑、绝望和厌倦不再包围我们,‘勇敢地活下去’不再是一句虚假而空洞的勉励。”评论家黄子平在随笔作品集《文学的意思》中如此写道。由读而评,由评而写,他借由文学的路深入繁芜的世界,用语言呼唤我们生命深处共同的古老记忆,直面人类共同的困境和前景。
《文学的意思》共分三辑,第一辑《文学的意思》是一系列专栏文章结集,旨在阐述文学的意义及趣味性;第二辑《边缘阅读》则希望阅读者能保持旁观者的姿态,并养成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策略,将阅读当成文本与意义的游击运动;因为“没有喜欢的害怕不是真害怕,没有害怕的喜欢不是真喜欢”而《害怕写作》是第三辑,惟愿今天仍有人喜欢阅读,仍有人敬畏话语的力量。

《文学的意思》
作者:黄子平
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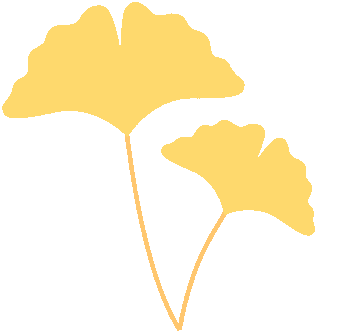
小引
作家们经常碰到的一个提问是:“为什么写作?”回答当然是“五彩缤纷”的,或严肃或真挚或激昂或抒情或幽默。据说,最聪明而又俏皮的回答是一句反问:“为什么不写?”
人们却很少想到要问问文学读者:“为什么阅读?”也很少想到,如果问到你,你会怎样回答?
显然,读的人毕竟比写的人多(有人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对这句开玩笑的话我们不必认真)。读者不一定写,作者却一定在读。实际上,在他开始写之前,他已经读过很多了。他的“读龄”比“写龄”长,正是文学阅读把他引上了文学写作之路。上路之后,也还是读书的时候多于写书的时候。“阅读先于写作”,不仅就作者个人而言是这样,而且就整个文学系统来说,也是这样。没有阅读的写作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写出来只是给自己读或心爱的人读。实际上,在作家一边写的时候,他就在一边读自己的作品。
大多数人都并非为了学会写作才阅读。我们只是“文学生产”的“消费者”。可是,当我阅读的时候,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作家的写作过程么?我不是在进行某种再创造么?“白纸黑字”不是由于我阅读的目光才“活”了起来,组织成“作品”吗?

米尔顿·艾弗里画作,下同
因此,作家们回答“为什么写作”时,实际上也隐约地回答了“为什么阅读”。他们的“五彩缤纷”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文学读者的回答。假如真的碰到有人屈尊向我们提问,我们也满可以既聪明而又俏皮地来上一句反问:“为什么不读?”
是的,阅读已成为我们理所当然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无法阻遏的愿望和需求。你会想起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一位关在单身牢房里的囚犯如何发狂般地读那本偶然落到手里的棋谱!阅读,是个人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接通”。只需回想一下那个“焚书坑儒”且规模史无前例的年代就行了。文学阅读是比文学写作更难以扑灭的“地火”,在岩层底下奔突、运行。在我们阅读的时候,“自由”回到了我们身上,饱受凌辱的心灵受到抚慰,被暴行和不公正所分离所隔绝的人们又在共同的召唤下聚集。在我们阅读的时候,日常的无聊、琐屑、绝望和厌倦不再包围我们,“勇敢地生活下去”不再是一句虚假而空洞的勉励。阅读,正如写作一样,都是以一个人的自由呼唤另一个人、另一群人乃至全人类的自由。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因为写作的人不惜劳驾动笔去写,这个事实就说明他承认了他的读者们的自由;又因为读书的人仅凭他翻开书本这个事实,就说明他承认了作家的自由,因此艺术创作,不管你从哪个方面探讨它,都是一种对人们的自由寄予信任的行为”。这样,企图奴役读者或讨好读者的写作不可能是真正的写作;同样地,只有不甘被奴役和不愿被讨好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
文学的媒介是语言。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实际上构成一种语言交流活动。而语言只能是“我们”的语言,“我”通过写作或阅读加入“我们”之中。在文学活动中我和语言互相渗透,“我”的界限被打破了,我开放自身,在与“我们”的交流中超越了自己的个体存在。语言本身是一个不透明的、深不可测的世界,其中积淀着一个个古老的民族的文化和内心生活。阅读使我潜入这个世界的神秘幽深之处,使先民们、父老们、兄弟姐妹们的痛苦、希望、愤懑和幻想汇入我的人生体验,我却消失在人类普遍情感的激荡之中,在刹那间沟通了永恒。因为我进入了那个从远古就讲起、还要世世代代讲下去的故事之中,我也成了这个唯一的故事的讲述者。它讲述人类存在的庄严和悲剧性,讲述灾祸、罪恶和死亡,讲述生命、爱情和青春,讲述已经走过的和还要走下去的漫漫长夜、漫漫长途……

阅读,正如写作一样,是用语言呼唤我们生命深处共同的回忆,正是这古老的记忆,把我们被日常分工所割裂、所隔绝的个人联结到一起,去面对人类共同的困境和前景。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的“意思”、文学的根本价值。当我们回答“为什么阅读”时,正如作家们回答“为什么写作”一样,实际上都是在回答:“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
当你与这个问题相遇之后,你的阅读就不再处于一种盲目的、被“灌输”、被诱惑的状态了。你成为一个自觉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读者。你寻求文学作品的“意思”,你创造它们,加入文学“意思”的生成之中。于是你开始关注在什么情况下作品是“有意思”的,“意思”是怎样在阅读进程中涌现和传达、组织和调整、老化和复活,你是怎样跟“文学语言”这个怪物打交道的……你发现,甚至在文学活动这样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里,人类通过如此复杂的写作和阅读,也在艰难地、坚韧地争取着实现着自己的自由。
你会想,是呵,“为什么不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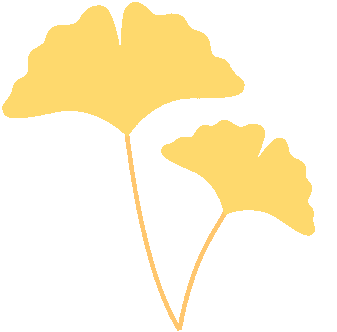
有点意思
我有一位同学,有人给她介绍对象。第一次见面之后,介绍人问她:“怎么样?”笑而答道:“有点意思。”此后的发展不消说得,自然是很美满的。
另一位同学,是写小说的。平时大家在宿舍里聊天,聊到热闹处,他会跳将起来,去抽屉里拿笔记本,口中念念有词:“这有点意思。”看来,又不知什么素材被他捉了去也。
发现“意思”,应该说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并不是到了谈恋爱或搞创作的时候,我们才瞪大了眼睛,耸起了耳朵。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只有十四天的婴儿宁愿看有图案的卡片而不去看“一张白纸”。一周到十五周的婴儿对复杂的图案比简单的符号更感兴趣。四个月后的婴儿尤其喜欢看人脸的模型,而不爱看拆散的积木。显然一张脸对婴儿说来是最有“意思”的,它意味着爱抚、进食、安全,或者相反。长大成人之后,从墙上的雨迹、树干上的疤痕、摘了门窗的土屋、半夜的窗玻璃以及在好梦或噩梦中,我们最容易“发现”的形象就是一张脸。

那些有“意思”的东西,总是与我们的生存境况最密切的东西。
在远古,我们的祖先(燧人氏和神农氏们)聚居在“山顶洞”中,不断地从一片黑暗中发现“意思”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那是什么?是敌人还是可以猎捕的动物?这种植物是可以食用的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到哪里去寻找可以敲出火星的石块?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仍在重复着同样的程序。红灯意味着“站住”,绿灯意味着“放行”;一个大感叹号种在路旁是“危险慢行”,一个骷髅头下边两根交叉的腿骨是“有毒”;爸爸瞪眼,说明想吃第五个蛋卷冰激凌的愿望落空了;老师扔粉笔头,说明刚才做的小动作被他看见了;小说获奖了,嗯,照这样写下去还能叫好;“挨批了”,——那就有点不妙,是不是上头又有什么精神?
对这些“意思”的疏忽,都可能不利于我们的生存。这种反应——倘要“寻根”寻得彻底——早在多少亿万年前的原始单细胞生物那里就开始了。这也许太夸张了。但这些单细胞生物能够从什么是有营养的和什么是没有营养的这个角度与它们的环境发生联系。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据说只是“一步之差”,但这一步是“世界历史”的一大步。生存,对人类来说,早已不单是一个“自然”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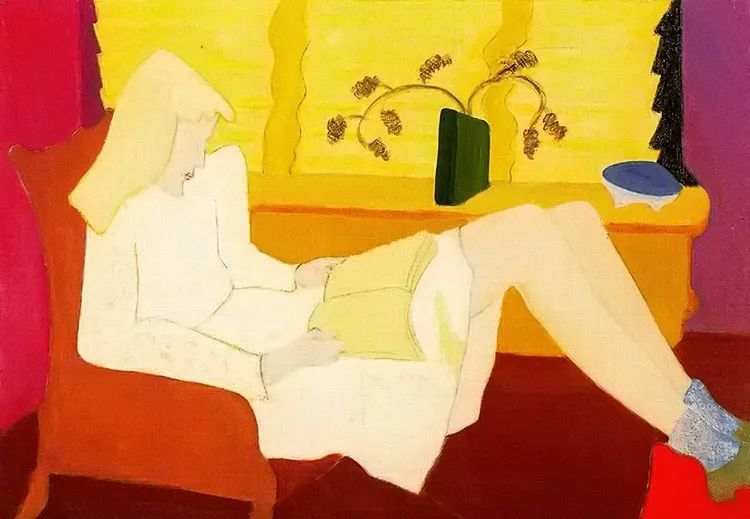
那么,当你在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却找不着“意思”时,会怎样呢?游园晚会上,你对着一个灯谜发愣;老师把你叫到黑板前去演算一个方程式,你准知道身后有好多幸灾乐祸的眼睛;某个古怪问题偶然闯进你心里,拂拭不去,却百思不得其解。诸如此类的境况之中,你会怎样呢?我会发出咒骂(出声的或不出声的),我感到焦虑,感到困惑,感到愤怒,我于是体验到一种挫折感。
可是,当你终于猜出了谜底,演算正确,找到了答案,你便解除了紧张,你享受到了一种快慰。发现“意思”的过程,常常就是一个由紧张而快慰的过程。当今世界上的无数赚钱或不赚钱的玩意儿,无不建立在这种人们心甘情愿地经由紧张而快慰的心理事实之上;魔方、家庭百秒知识竞赛、九连环、推理小说、侦破影片、“欲知后事如何”,等等。你相信案子总会水落石出,凶手总能捕获或击毙,好人定有好报而有情人终成眷属。挫折总是暂时的,合理的结局迟早要奉献在你面前。编导和作家不过是在“卖关子”,他们知道这能卖钱。六岁的孩子也晓得在电视机前安慰奶奶:“别着急,会有人来救公主的!”
在日常生活中,可没人担保到了“下回”就定能“分解”。猜不出的谜、解不了的方程式、找不到答案的题,多的是。并不是每一件失物都有人招领,许多恶人也得享天年,寿终正寝。有时人们会问你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屋子着火了,先救你妈还是先救你老婆?诸如此类,不是没法回答就是很难回答,你怎么办?你会嘟哝一句:“无聊!”然后溜之大吉。你把它们“搁一边儿去”了,对之敬而远之。第一个问题不管答案怎样,都不影响我吃鸡或吃蛋。第二个问题,唉,到时候再说吧,当然,要做好防火工作……

但是,许多时候,有些问题没法“搁置”。它打上门来了,它迫在眉睫,不容忽视。需要面对着它,跟它肉搏,需要把那点“意思”弄明白。高考试卷上的一道大题(25分!),事关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你玩儿了命也得把它做出来。如果哪里出了毛病,你会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解题的步骤,找出可能疏忽的地方。要是绞尽脑汁、精疲力竭也还找不出毛病,你就会变得十分绝望、恼怒、沮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程度不一地,会陷入这位倒霉的考生的境地。在应该有“意思”的地方找不着“意思”,我们说:“全乱了套了!”下水道不知在哪里堵住了。没停电,保险丝也好好的,可是灯不亮。领导对你不满意(这次涨工资又没你的份),可又不知为什么。丈夫变得冷淡起来,是不是有了“第三者”?稿子退回来了,退稿信还是那几句铅印的套话。理想破灭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写封信给某杂志:“生活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
小问题找不着“意思”是小麻烦,大问题找不着“意思”则是大麻烦。焦虑可能发展为危机感,发展为心理的失调、病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过去采取的步骤,被心理学叫作“偏执”。用言语和行为表现出粗鲁被称作“敌意型”。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叫作“忧郁症”。把事情的好坏归因于天意或别人的阴谋,这叫作“妄想型”。退缩到自己能够控制“意思”的纯幻想中去,这叫作“压抑型”。在生活中丧失了必要的“意思”可能导致伤害他人或伤害自己。
大多数人都能容忍自己生活中一定数量的没“意思”或杂乱无章,否则,你真的没法儿活。人们在习以为常的“意思体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自得其乐。那些硬要在没有“意思”的地方找出“意思”来的人,比如为一个什么“猜想”写了六麻袋稿纸的数学家之类,常被人视为“疯子”。而那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写什么“梦”的落魄文人,也自我感叹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惹得天底下不少痴男痴女,也陪着掉了不少辛酸泪。

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必要的“意思”的人,和不满于既定的“意思体系”,致力于发现和创造新的“意思”的人,其实是两类不同的人。但是人们常常混淆不清,一律以“痴”“傻”“狂”“呆”称呼之。
文学艺术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对世界的一种把握的产物,是他们对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的一种表现。意味深长的是,它们有时候作为日常生活中“没意思”的部分的代替物或补充,有时则作为这“没意思”的部分的逃避或反叛,而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于是文艺作品常常是某种“荒唐言”与某种“其中味”的古怪统一。
可是,无论如何,文学作品是被人们普遍地认为必定有“意思”的东西。生活中许多没“意思”的东西我们可以容忍,但如果说某部作品“毫无意思”,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指责。所谓“意思”,依据不同的理论,可以理解为“主题”“思想意义”“韵味”“境界”“好玩”,等等。白纸上的黑字排成了行,这就是说,总要告诉我们点什么。寻找“意思”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小学里语文老师又教会了我们怎样归纳课文的“主题思想”。长大了,我们听说“主题的多义性”有可能比“主题鲜明”更棒。甭管“多义”“单义”吧,反正一篇篇自命为“小说”“散文”“诗”的那些东西,理所当然地是应该蕴含着“意思”的。如果找不着,我们会说:“令人气闷的朦胧!”

其实,无论是明白晓畅的作品,或艰涩难懂的作品,还是故弄玄虚的作品,都是建立在我们这种认定只要是作品就会有“意思”的心理之上的。契诃夫有一篇小说,公然标题为《没意思的故事》,他知道读者决不会因此掉头而去,恰恰相反,这位读者翻开书一看:“哎,《没意思的故事》,真有意思!”读完了一想,果然这小说是大有深意在。
我们的头脑顽强地固执地要从认定有“意思”的地方发现“意思”。有一位反对“朦胧诗”的批评家曾经做过一个很得意的实验。他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里胡乱摘了几句诗,再从雪莱那里摘了几句,又从当代某青年诗人那里摘了几句,像洗扑克牌一样打乱之后,排成一首“诗”,然后拿给一位“朦胧诗”爱好者看。这位无辜的爱好者连叹“好诗!好诗!”这个实验确实是很有趣的。读者诸君不妨重复一下,但要尽可能多排列出不同的组合方式来。你会惊奇地发现,在这样胡乱拼凑出来的“大杂烩”里,至少有一多半是能够“看出点意思”来的,而且既俏皮,又新鲜,蛮有“现代味”。你的头脑参加了“诗”的创造,你在填补诗句与诗句、词与词之间的空白,你在整理杂乱无章的字句时加进了自己的“意思”。
我无意推荐一种制造艺术赝品的速成技术。我只想说明,现代艺术尊重并且力图激发读者的这种创造性。划分什么是严肃的艺术试验,什么是故弄玄虚的造作,似乎越来越困难了,但标准总是存在着的。作家应该把读者对浑浊、膨胀、杂乱无章的“耐受能力”估计在内。他必须在纷纭复杂与有机和谐之间寻求一种不那么可靠的平衡。他相信,他的编码方式是能够被一部分译码的人们所接受的。谁愿意自己的作品被所有的人“搁一边儿去”呢!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有意思似乎也不可能。智利诗人聂鲁达说过:“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这是相当可悲的。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就连驴子也懂得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我们中国的大画家齐白石说过大致相同意思的话:“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

至于我们,作为读者,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易抹杀自己“不懂”或“不习惯”的作品。如果我们不愿意花费精力去习惯它或弄懂它,也大可搁置了事,不必表示愤怒或者沮丧。但是更好的方式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艺术家只是以他个人的方式对人类的共同生活做出反应,我们依据自己的生活多多少少也能理解这种反应。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里,又不会满足于生活在一个仅仅是可以理解的世界里。那些善于发现新的“意思”的人,善于创造新的“意思”的人,扩大着我们的视野,赋予我们新的眼光,去认识世界,认识我们自己。这些人,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人。
原标题:《成为一个自觉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读者,去发现“文学的意思” | 此刻夜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